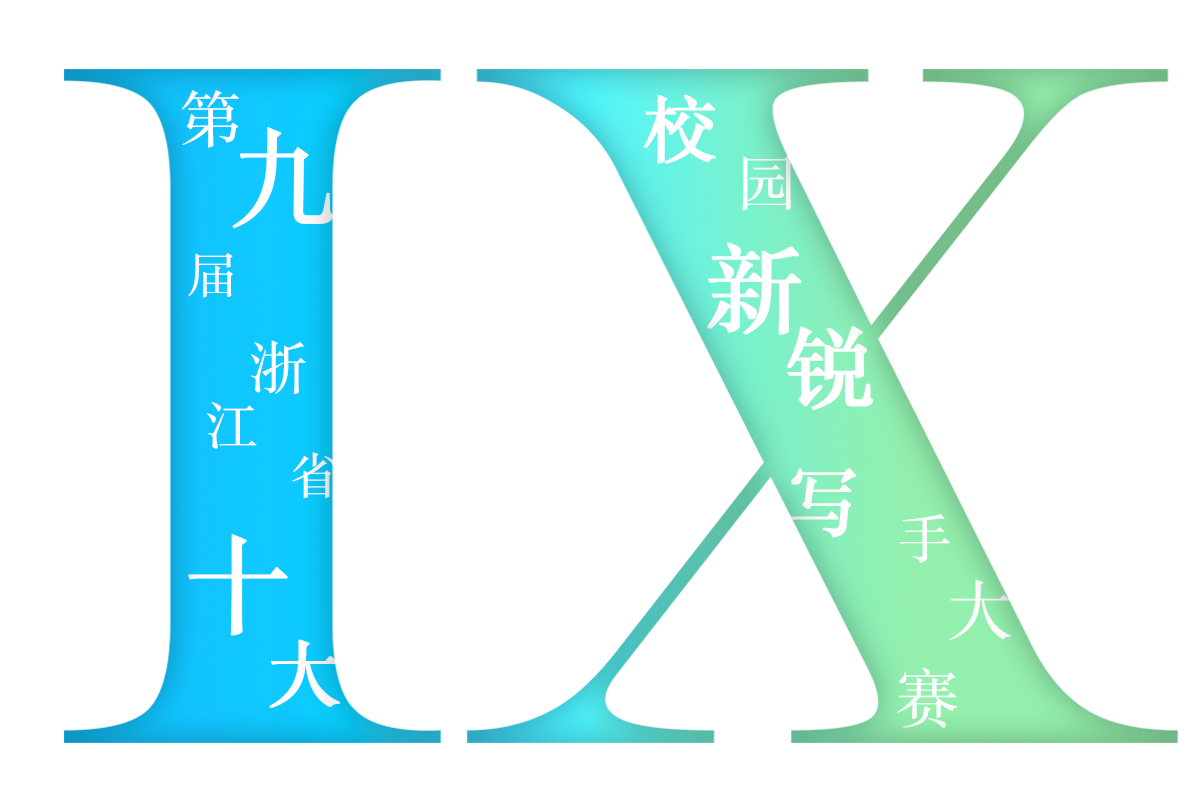追寻身份认同之旅 ——解读《故乡·鲁迅专集》的鲁迅内心世界
beatrix 发表于 2024-06-12 22:19:16 阅读次数: 166追寻身份认同之旅
——解读《故乡·鲁迅专集》的鲁迅内心世界
早在看《觉醒年代》这部剧的时候,我就觉得鲁迅先生对当时的北京政府有着极度的不满。他愤其懦弱,怒其不争,对外被列强侵略,对内国内军阀混战,封建制度依旧,人民生活水深火热。所以在读鲁迅先生的《故乡·鲁迅专集》时,难免会带入他当时的失落难过心情。20世纪20年代初期,鲁迅先生生活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因为找不到国家的出路,处于极度苦闷中的鲁迅当时心境很颓唐,但是对理想的追求仍未幻灭。他想战斗,却又感到孤独、寂寞。在北京的他,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在这迷茫、困惑的时期,他回到自己的故乡,希望在自己的故乡重拾心灵的慰藉,找到身份的认同。
自我归属的身份认同
因在北京郁郁不得志,所以鲁迅先生趁回乡售卖老屋之际,踏上寻找归属感的道路。
在《故乡》一文的开头,鲁迅先生写道——
“时间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有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点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
通过景物描写“萧索的荒村”“没有一点活气”“悲凉”看出故乡是苍凉的。入乡时的灰色陌生感给鲁迅先生在故乡寻找归属感的困难做了铺垫。
文中处处可以看出先生所到之处,所遇之人,全没给他带来喜悦之感,在与邻里乡亲相处几日后,竟是想急着收拾行李,尽早离开。
在《孔乙己》一文中,同样提到鲁镇这个关键地点。这是鲁迅先生的故乡。但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鲁镇的人和事,对主人公孔乙己以及他身边的鲁镇人是持批判态度的。
《孔乙己》写于1918年冬天,而科举制度虽已废除,但是培植孔乙己这种人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这样依然会产生新的“孔乙己”,而鲁镇人的麻木落后,深刻体现当时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毒害和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这个“鲁镇”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样的故乡如何让他找到认同与归属感?
而在《药》、《阿Q正传》等小说中,地点的设定,应也是以鲁镇为基础的。鲁迅先生在文中用尖锐的文风,犀利的笔调将人和事的迂腐、麻木、可笑刻画得一览无余。可见在这一系列的小说集中,鲁迅先生一直都在反思故乡的愚昧和世故。身体虽回到故乡,但思想却与故乡格格不入,这种“无归宿”的情感体验让他非常矛盾。表面上是回到了家乡,但是思想上却感觉“无家可归”。这趟回乡之行,让想寻找自我归属认同的鲁迅先生无比失望。
以杨二嫂为代表的乡土身份认同
杨二嫂的出现,就是一个鲁镇小农思想典型人物的塑造展现。杨二嫂是一个被当时社会侮辱、损害而又深受小私有观念支配的小私有者形象。但她只是众多类似形象中的一个缩影。
从鲁迅先生对杨二嫂外貌的描写“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双手插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的细脚伶仃的圆规。”可以看出先生对此人的态度是鄙夷的,甚至在文中接下来大部分都不用“伊”,而是直接用“圆规”这一称呼来替代她。
其实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鲁迅先生虽然极力想在邻里乡亲们身上找认同感,但是他的内心却是抗拒的。他笔下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就透露了他的情感走向。
杨二嫂在得知鲁迅先生要变卖家里的器具时,就直接顺便将鲁迅先生母亲的一副手套塞进裤腰,可见她竟将偷窃这事做得“行云流水”了。
在文末,杨二嫂以在闰土的灰堆里发现碗碟为由,告发闰土,以此邀功,还未等主人家发话,便抓起“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鲁迅先生讽刺她道“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还跑得这样快。”其实杨二嫂就是在“明偷暗抢”。
杨二嫂是一个当时社会被损害的民众的形象。二十年前被人摆布,以色相招徕顾客,被称为“豆腐西施”,随着社会变迁,不但外形改变,人格也发生变化——庸俗贪婪,明偷暗抢,尖酸刻薄,泼辣放肆。
而文中类似杨二嫂这样的鲁镇人可谓比比皆是。母亲对鲁迅先生提及闰土时,说了一句“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而鲁迅先生在鲁镇留下来的剩下几天,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他,可是他却一面应酬,一面忙着收拾东西,想尽早离开。文中虽然没有对本家和亲戚做过多描述,但是可见先生已经觉得自己完全无法融入这一类人群。
杨二嫂这类鲁镇人,其实是鲁迅先生笔下这个日益衰败的畸形社会的产物。他们身上的坏习气主要是生活的压迫和封建统治阶级精神毒害的结果。
全文下来,可见鲁迅先生对寻找鲁镇这个曾经故乡乡土身份之认同已经完全失败了。
反观杨二嫂,她面对鲁迅先生也是冷嘲热讽。自他去北京做学问后,她的内心早就不再接受“鲁迅先生依旧是鲁镇的人”的观点了。
因离乡多年,鲁迅先生已不太记得杨二嫂,她就说“忘了?真是贵人眼高。……”,还说鲁迅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甚至还想贪小便宜,把鲁迅先生家中变卖的东西带回家。鲁迅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嘴,默默地站着。”我认为鲁迅先生完全可以辩驳这类的无稽之谈,但他没有,因为他应该是不屑与这类人解释。
在《故乡》中,杨二嫂应该是一个典型鲁镇人民的形象。相信像她这样认为“鲁迅先生已经不再属于鲁镇”的人不在少数。
鲁迅先生在故乡无法找到自我认同的时候,寄希望于同乡的乡土身份认同,但是他既无法接受同乡,且故乡的亲邻们也无法再接受他。在彼此都无法融合的情况下,鲁迅先生的乡土身份认同之希望也面临失败。
以闰土为代表的童年回忆的认同
在寻找自我归属的失败和在追寻乡土身份认同的希望破灭后,鲁迅先生最后把寻找认同感的希望寄托于童年回忆之上。
他于《社戏》一文写下“一直到现在,我是在再没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可见昔日的故乡是鲁迅先生的精神慰藉,那里是温暖的,甜美的,是心灵的栖息地。
但是在《故乡》一文,首先在鲁迅先生关于外貌的描写,就可看出童年回忆在慢慢散失。
鲁迅先生在描写闰土现在的外貌时,“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变成 “灰黄”且有“很深的皱纹”,“红活圆实的手”现已成为 “松树皮”。这里的对比描写,充分展现出闰土被窘迫的生活所摧残,也可看出闰土历经沧桑。
当鲁迅先生想跟他聊聊近况时,“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看到闰土经历太多苦难,人已变得麻木。所以鲁迅先生才会说他“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在闰土喊出“老爷”那一声时,鲁迅先生又说“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很明显看出,闰土因生活在底层社会,觉得人要分为三六九等的封建思想已深入内心。
当《故乡》一文末尾,闰土快离开时,鲁迅先生在文章里写道“我们终日很忙碌,再没有谈天的功夫。”我认为,其实这里的“终日很忙碌”只是先生的一个借口,因为“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他们已再无共同语言。
到这里,鲁迅先生觉得自己想在童年找到归属感的希望不太可能。闰土是一个在旧中国受尽摧残,却还尚未觉醒的农民形象,他不仅仅生活穷苦,且深受等级观念的束缚和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也是善良农民群众的一个缩影。
当鲁迅笔下写道如今的闰土“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肿得通红”,我可以联想是不是闰土的父亲也曾经像小时候的闰土那样活泼可爱,与鲁迅先生的父辈一同玩耍。这样的轮回是不是在这个残酷的社会下已经有好多轮了?
就此,鲁迅先生回到故乡,去寻找身份认同的希望彻底泯灭,发现他终究是他是无法融合到这个落后愚昧的社会中去的。因为那“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而已。就像他在回忆录《朝花夕拾》的《小引》里写道的那样,那也只是童年的“蛊惑”。
小结
《故乡·鲁迅专集》写下了当时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而人民群众在精神上的病态束缚,也扭曲了他们的人性,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麻木。鲁迅先生在回乡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中,虽然没成功,但他并未失去希望。在侄儿宏儿与闰土的儿子水生之间的情感互动下,他把希望寄托到了新一代身上,并决定要努力去突破现有的困境,重新找到新的出路。所以在《故乡》的末尾,鲁迅先生写下了——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也印证了鲁迅先生一生都在追究真理,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在经历各种失败与探索后,最终成为了一名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为此战斗一生。同时也找到了自我身份的最终定位和认同。
本文参考文献:
(1) 鲁迅《故乡:鲁迅专集》(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同心出版社)
(2) 鲁迅《故乡》(浙江文艺出版社)
(3) 钱理群《鲁迅入门读本》(中国长安出版社)
作者:孔依谦
学校:温州市实验中学七16班

 |

 |

 |
范德清 |
张利利 |
汪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