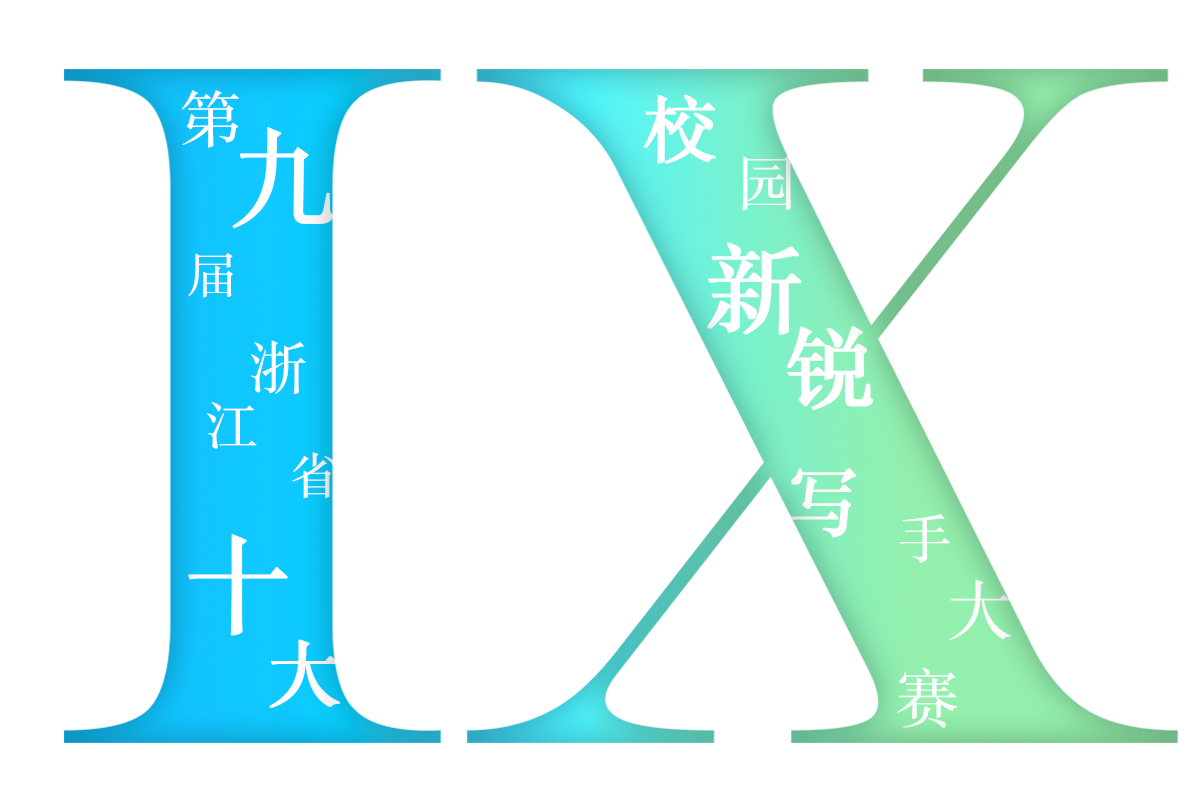阿司匹林
lhyy 发表于 2022-07-31 20:35:29 阅读次数: 29471外婆终于答应搬家了。
她本来就住得偏,虽然那里生得安静,但从外公走了之后,这房子就“生锈”得越来越快,受潮的家具,脱漆的门窗,不断积累的疾病,一切的一切都催促着外婆重新进行生活的组装。至少爸爸认为这暗示着要让外婆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而什么生活的结构、重组,在妈妈面前最后只是一个凝固的定点。
“搬完之后是方便了你,但妈的心你搬得了吗?”
每次提起这件事,妈妈一直是摇头。这房子是外公建的,他们接近三分之二的人生塞进了这个暗褚色方形容器中,我们也不知道那里的每个角落藏了多少故事。可能外婆每次对爸爸的提问的沉默,自己注射药物的熟练,还有对每件弥散着陈香的檀木家具的轻抚,让妈妈在与爸爸每次的争论中都占了上风。
但即使是在我的理想主义中,在选择载体的天平上,准星也总是移向生活的振动。在爸爸第四次劝说外婆的时候,外婆居然答应了。所有人都知道爸爸应该多说了什么,却不得而知。我也只是从那模糊的表情,依稀才出了那句话。妈妈也一点知道,但也只能用无言的愠色表现自己的最后的不满。
爸爸忙着给搬家公司打电话,我和弟弟随意的走进了外婆家附近的一家鱼丸店。只是当我看清了店名和便利的装潢,才发现这是在我出生前就有的那家小时候经常去的店。但是当我看见若干年没见的老板娘,我的一小瓶理想主义随即被打翻在地。
突然身侧满嘴油光的弟弟和我说,外婆肯定是因为这家的鱼丸才一直不搬家。说完给趴在椅脚边的那条小金毛扔了一个鱼丸——它叫小黄,原来是养在我们家,后来怕外婆一个人太孤单,就送到外婆那边。虽然现在它已经很大只了,但我的理想主义和预备小学生的稚心不谋而合,还是想叫它小黄。
我对弟弟的话摇了摇头,没想到他却一定要我说出我的想法。我也只是搪塞:
“我们家离医院近,给外婆买药方便。”
“什么药?”
“……阿司匹林。”我没敢看他。他应该是定了点头。
我简直在乱说一气。
我用勺子搅拌着已经凉散的汤水,鱼丸时不时碰撞着碗壁。突然戳进了一个鱼丸,里面一点温热的汁水被溅起,我的心一颤——可能伪装最后都会破碎,我所抱紧的东西只是生活膨大的外壳。
每天我都担心弟弟会发现什么——爸爸总是一身黑西装,妈妈则是前天晚上熨过的平整的白衬衫。爸爸的鞋放在玄关左侧,妈妈的鞋放在右侧。听到的永远是两次关门声,他们不会同时出门。爸爸乘地铁,妈妈开车——爸爸总是踩着家里黑色钟表的整点到家,妈妈回家的时间是一条没有周期的函数,带着被车鸣路拥抹上的倦怠。没有起伏的对话,只有在餐桌上几句对弟弟不约而同的关心。
看到弟弟没有什么反应,我想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可能是我在白昼的竭力逃离让我神经元不断增加,一切相关的波动都被我的神经末梢不断放大。我大概已经接受了这一处的坍塌,却想要荒诞地逃避混沌。
只是从鱼丸那天起,弟弟就一直向我要阿司匹林,那个“可以让外婆放弃鱼丸而且带回小黄”的神奇药丸。我只好随手在储食柜里拿了一瓶某品牌新口味的硬糖,并且告诉他不要乱吃——不知道他如果烂牙又要耗费我多少精力。
有一次他的玩具车找不到了,他就在玩具柜那个空缺的位置放了一粒“阿司匹林”。不到半天,玩具车就在外婆打扫卫生时出现了。大概是从那时起,他对阿司匹林的功能坚信不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那罐东西。在那个夏天,我们一家去了海滩玩,他看见有一只断了腿的螃蟹在被海水浸润而粘重的沙坑里挣扎,就从小罐子里取了一粒糖放在螃蟹旁边,埋头嘀咕:“你一定可以爬出来的。”当恣肆的阳光几乎融化了屋顶的一角,他出了玩具店,却在一只小狗前停了下来——一只趴在商店门隙前,吐着舌头,急促地喘着气的黄灰色小金毛,哦,它身上的灰色应该是泥灰来着。弟弟先是把糖放在它跟前,又好像想到了什么,把糖放远了些:“你是不是我家小黄的亲戚?这粒药你不能吃,它可以让你变凉快的。”留下小狗紧紧盯着那粒白色。不知哪天,他甚至给了外婆三粒,叫她转交给鱼丸店的老板娘,因为他还是忘不掉那味道。
当他小心翼翼的向我要第二瓶时,我和他说这是最后一瓶了,他把罐子抱在怀里,透过玻璃的罐壁看见他衣服上那个英雄已经被压皱,英雄脸上晕开油渍,看不清表情。他抱得很紧,练哪几个小小的指甲也泛着乳白。我不知道他用阿司匹林做了多少事,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但我总觉得在无数个夏天的事件里,他已经在生活的白昼释放了足够的积极因子,他应该是快慰的吧,至少在他用尽最后一粒药丸去阻止黑夜降临或者在药丸失效之前,应该是这样的。可我还是隐隐地看见了那无处躲藏的喧嚣。
这几天晚上的月亮都被云絮剥蚀,没了光亮,连天空都显得惴惴不安,落地窗里的风景也变得颠簸。外婆自己注射完药剂已经入睡了,当我从弟弟的房间出来,想着现在这个时间去喝冰箱里的柠檬水怎样才不会被妈妈发现,从不远掩映的光亮中,木制相框的落地和玻璃的破碎划破黑暗,刺激着我的耳蜗。我立马带上了门,不想惊醒床上的安恬。虽然我的神经好像始终不会适应一切的碎化、撞击和分裂,但我的心早已习惯了,此刻只是突然想明白为什么要给比比的房间装上隔音板,也知道黑夜这时才真正降临。我转头看了眼客厅里的小黄,它只是在颤抖着,埋下头,低垂着耳朵,对着角落低声呜吠着。
激烈的争吵声抵着桧木门框,像两块干燥的木头在燃烧,我在床上甚至能闻到飘散的烟味,而最后总是以訇然的开关门声喝完间歇明暗结束。我躺在床上,只是想着,至少白天是安然的,至少只是明与暗,没有红与银,至少我们还共享着同一个近乎密闭的容器里的空气,至少他们曾经爱过——我其一的价值大概就是证明这一点。我没有在辩解什么,只是为了此刻的安眠。
外婆对这些也肯定心知肚明,至少是因为她的房间没有隔音板。但她好像一列脱离轨道的绿皮火车,在这个匆匆的家里缓慢行驶,却也总是靠站等待。虽然还不适应房子里人的密度的增加,但是楼下的菜市场已经成了她的出行选择。本来的午餐,大多数是妈妈给我们订的外卖,可自从外婆来了,死气沉沉的厨房飘出了桂鱼的鲜香,连那锅气和灶火都透着一丝温和。我们当然对没有塑料餐盒味的饭菜十分欢喜,而外婆即使有时忘了开油烟机被呛到依然乐在其中。妈妈知道了,一边想要让外婆多休息,一边又不想打扰了她的生活兴致。
可能随时分开生活了太久,她们之间总是流转着一种陌生的熟悉,妈妈对外婆的关切一部分随着工作和情绪流失,剩下的全部折叠进几句普通的问话中。外婆晚上会多做一道菜,多放一点米,摆好碗筷——她在车站停靠,只是大多时间,啊妈妈只是错过或是没有坐上这班火车。我对这些生活段落只能摇头。
夏天的风终究是过去了,虽然留下来些许焦味。但是秋天却放纵地烧毁了一切。弟弟上学的第二个星期四,避开他,爸妈向我和外婆扯断了那根绳。房子给妈妈,因为妈妈要照顾家里三个,车给爸爸,虽然他早该脱离地铁的拥热。至于小黄,我只开口说了一句,让小黄在留几天——可能是为了弟弟,可能是为了我道不明的理想主义。
家里没有了爸爸的痕迹,玄关左侧只是一排拖鞋。原来挂黑色西装的地方挂的是妈妈的呢子大衣。至于冰箱里,没有了啤酒,会有妈妈偶尔和的鸡尾酒和我藏在最下面的柠檬水。可能唯一留着他的气息是书房里的黑色书桌。弟弟自然会问起爸爸的踪影,我们统一口径说爸爸去外地出差很长一段时间,弟弟似乎没有怀疑,只是和小黄玩着扔接球游戏。
其实对弟弟来说,可能小黄的离开才是最大的痛苦,因为这件事没有理由。那一天,我只能装作带小黄出去遛弯,把它交给等待的爸爸。在红色皮绳被接走的那一刻,我也是失落的。面对弟弟疯狂地追问,我只能一遍遍冷静的说小黄走丢了。那可能是他六年生命中透露出的最强烈的慌乱和紧张,没有放声大哭,只是跑下楼不停的寻找。我只能在旁边看着他,看着他有没有摔倒,一直到看见他的汗掉进半边夕阳里。
之后每天放学以后,他都会重复地寻找,虽然都是失望而归,但只是抿紧嘴唇,好像坚定地相信着什么。宠物离开的气氛渐渐地消失,而这让他不再深究爸爸的事,这似乎是我们所期望的,生活的漏洞好像在被修补着。
直到我已经习惯只分泌静谧的某个夜晚,细小的啜泣声和明显被抑制的咳嗽声还是刺激到了我永远敏感的神经。来到客厅,摸索着打开灯,努力睁开还没适应的眼睛,我只是呆滞地望着那个角落。
小黄留下的蓝色的狗粮盆被装满了白色糖果,再放一粒,这场沙塔游戏就会结束。弟弟只是开在墙边,盯着它抹眼泪。我快步走向他,蹲下与他同高,而他趴在我肩膀上稍稍提高音量:
“为什么?我明明每天都往哪里放一颗阿司匹林,我还怕它作用太小,每天吃一颗。心里想着小黄快点回来,可是现在那里都堆满了,为什么小黄还是没回来?”
我的皮肤渐渐触到冰凉,让我回到以前的每个夜晚,打破原来每天喃喃的自我安慰——其实当我在担心妈妈对自己和冰柠檬水的斥责是=时,她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我,只是在怨愤地自我燃烧。本来说至少到高中结束之后再解决的事,在这个秋天就改变了我的生活轨道。其实我也想在隔音的房间里睡觉,想要一个可以消解怀疑的永存的梦。其实我也哭过,只是最后都成了脸上毛孔吸水后的膨胀。
好像是在安慰弟弟,但又是自顾自地重复着课本上的那句话:“阿司匹林服用过量会引起水杨酸反应,会引起头晕、耳鸣、肌肉酸痛甚至精神混乱。”
阿司匹林不是万物解药,他只能解热镇痛,或者唤醒记忆,或者自我清醒。
或许是对生活的希望已经变得成熟,面对生活给妹妹设计的略显荒诞的错乱也只觉得是浮动的光点。妹妹接着不断的电话,处理着无数的文件,咬着一片面包,不再在镜前停留。,慢慢的,妈妈身上多出的地铁味让我枯萎的想象感到安心。每周一次与爸爸的视频通话消解着弟弟的怀疑。明明更加忙碌,妈妈却总是准时出现在晚饭的餐桌上,家里药柜上的药物都贴好写着注释的纸条。妈妈偶然一次的出差,每天晚上八点,外婆微微陷进沙发里,接着妈妈的电话。每次看见外婆在房间里用注射器想松弛的皮肤里注射药剂,提到蹒跚的拖鞋声,我都希望我全部的理想主义都作用在外婆身上。
我有时会画画——下雪了,那列绿皮火车依然在行驶,每天总有一个人在起点站上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下雨本来是过着柏油路的泥土味和窗口樟叶的清香,差不多可以成为一个人们为生活痴癫的理由,但是和尖锐的车鸣与喧嚣的尾气在傍晚玩这个时间点掺在一起,它的享受价值就会不断萎缩,甚至分泌麻烦。果然,外婆的药剂用完了,医生说这药停一天都会对老人有影响。这个时间,大概可以赶得上医院的灯。我先在家里尽力地翻找,侥幸地想会有多的药剂。当我检查书桌的抽屉,拉开最底层的那个没有上锁的屉格,意外地听到了滚动和碰撞的声音。弟弟剩下的所有糖果都被放了进去,充斥着微潮的甜味。
旁边放着一张发皱的纸条,上面只有歪斜的一串拼音,我尝试着读出来:让爸爸快点回来。
我不敢动那瓶糖果,因为那好像不是我所能摆弄的——我以为白昼里的是一个在膨胀的花丛里奔跑的无名少年,其实他咋吸收着白与黑共有的颗粒,即使让喉咙流血,也会无限呼唤。
我最后给妈妈打了电话,她说马上回来。六分钟后,利落的钥匙声带来了打开的门。比平时提前的这个时间点没有顺路的地铁,早上出门没有带伞,这点路程她更不会打车,所以 原本干练的短发贴在耳后,衬衫的边角也被浸润,脸上的水滴不断流进一张一闭的嘴里,她只是招手,叫我把外婆扶出来。弟弟执意要跟着走。
四个人挤在出租车的后座,我只能缩紧肩膀,但妈妈身上黏凉的雨水仍旧染着我的衣服。车向左又向右转,我们四个一起向右向左倾靠。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我转头看向身边的人,突然发现,现在我的理想主义就只存在于这狼狈有紧密的四个人里。
可能我依旧会按时给生活服药,可能阿司匹林永远解决不了生活的一些头痛和炎症,但我会找到我的坐标,做好线性规划,绕开那些漏洞。
可不可以给我一片阿司匹林,为了在白昼尽情横冲直撞,为了让黑夜也渗透进清醒,为了我永远不灭的理想主义。

87

88

88

87

87

89

90

80

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