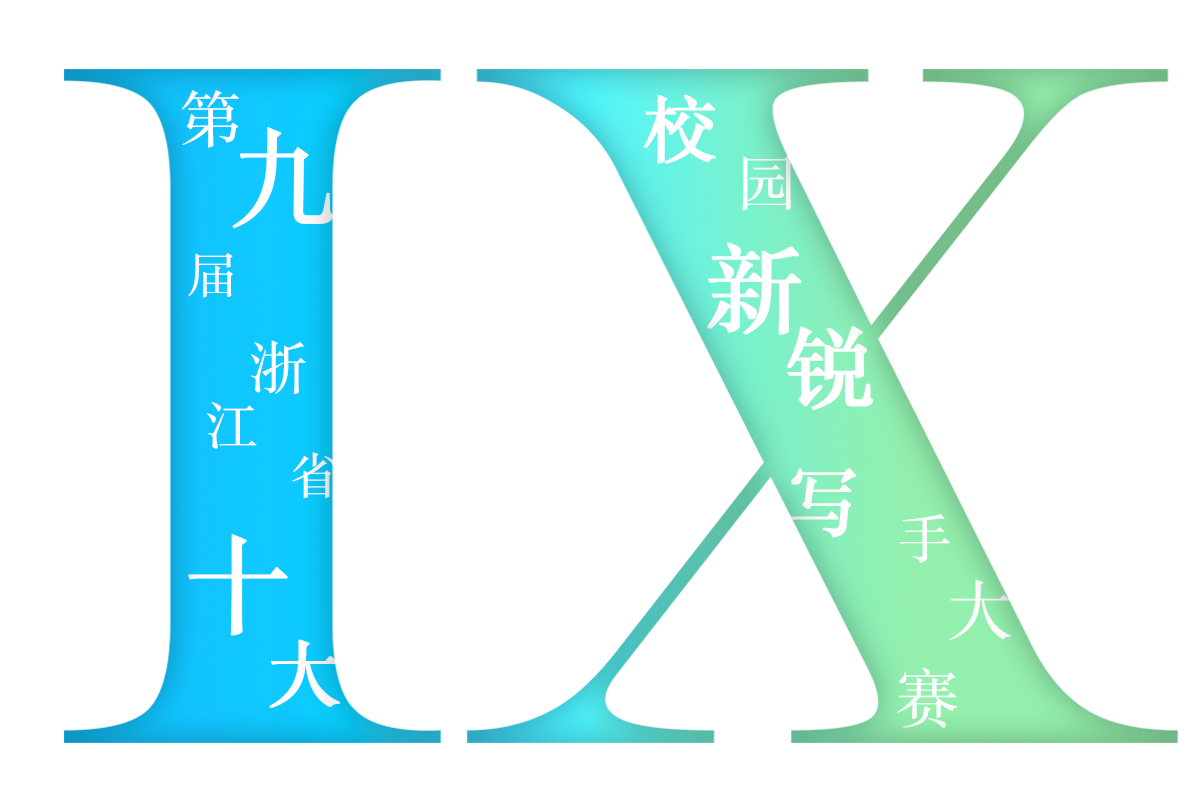佛香缭绕
mu沐 发表于 2024-05-02 21:04:55 阅读次数: 856阿妈要带我去村子南边的寺庙。
说是村子,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在外地讨生活,留下的几家人都是不愿去外头的。如果将村子比作城市的夜晚,那只用肉眼就能晓得庞大的暮色里只残留了几颗星子。
打我记事起,每逢初一、十五阿妈都要拎着一袋子贡品去村子北缘的寺庙里祭拜。 寺庙的历史久远得难以判断它的年龄,仿佛它是凭空从一片翠竹包裹的空地里拔地而起的。没有人在意它经历过多少个轮转的四季,自张骞开西域后就是如此,将它视作日常的一部分。
“成家前要先盘算柴米油盐酱醋茶,过日子后就得要诚心礼佛”阿妈将这些话告诉我,村子里不会有人批评它身上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我于是懵懵懂懂地默认它的正确,像太阳升起一样合理。
寺庙隐匿在一围湘妃竹里。远远望去,门户被南方充沛的雨水刮得斑驳不堪,堂前有一口子铜铸的钟,也是黑漆漆一片,几乎与人们眼中的古寺应有的样子雷同。正因为它的院落过于陈旧,这座寺的香火一直不怎么旺,平日只有还长居在村子里的人才会在初一,十五时进寺祭拜。我们都不怎么喜欢去那,竹林深处很少见到阳光,阴森森的,类似港片中鬼怪出没之地。
尽管如此,寺院还是住着两个和尚——正好一老一少,老的那个自然是方丈,年轻的是前些年里被老和尚带回来的。 老和尚原来就是我们乡里人,听说他还没出家时去外面闯荡过,大概是赚了不少钱的,可惜后来家里人一连串地走了,剩他一个孤零零的。再后来他就皈依佛门,在小寺里做起了和尚。
寺庙虽小,五脏俱全。推开古朴的木门便是前堂,前堂容下一尊大鼎,供人们烧些纸钱,鼎是很久前有心人好意赠予的,用铁铸成的鼎壁薄薄地铺上一层铁锈,如同肉松面包上涂抹的一层番茄酱。往后走是几尊花相的铜铸佛祖,原本画上的色块脱落得不成样子,青一块黄一块的,像是佛祖摔了一跤。佛像前是两条长桌,两边各摆上一组蜡烛,几盏油灯。长桌后头放上短桌,摆上满是灰的香炉,便算作供台,倒也显得整洁大方。自不必说的是扫地,续烛火这些琐事,都归小和尚管,大部分时间老和尚都在后堂礼佛——我见过那本翻的满是褶皱的佛经,每一页都带着岁月的斑黄,但还是很整洁,足以看出老和尚对它的珍惜。
十五的日光并不黯淡,空间似乎蒙上一层粗糙的亚麻,早晨的土路被露珠润湿了些,走过去响起竹枝断裂的清脆响声,我牵着阿妈的手,阿妈肩头挎着一袋子贡品,她大概觉得有些重,我们就一直沉默着。走近寺庙前的路口,竹林里的风卷着叶子拂过,我的脸被划出几道细痕,可并不觉得疼,阿妈也没注意到。我俩继续向前走,不一阵子,就看到一座小小的寺庙突兀地出现在竹林里。
我被阿妈拉进庙里,周围的环境对我而言并不陌生,一切都和小时候的记忆一般陈旧。我没心思看阿妈祭拜的过程,低着头想象寺庙刚刚建成是该会是怎样的景象——尽管在这个南方的偏远村落,但依旧被香火散出的烟雾笼罩得严严实实,似乎盖上一层雾霾也比不上的厚实棉被。来往的村民正络绎不绝地参拜新铸的佛像,身长两人高、宽三丈,一体泥塑佛身镀着灿黄色颜料,媲美他处的镀金佛像。此后它便成为村子文化的象征,每每提起故乡我们总会想到它,大概是它的存在让空荡荡的村落多了一段清楚的过往。
她见我呆在原地,于是用手拉我深色米老鼠印花的T恤,说道:“快点跟我进去!拜完佛祖还有别的事要办,你也要学学怎么拜,将来你也要来拜的”我点点头,缓慢地在泥地上踏出几个鲜明的脚印,当时的我觉得它代表了我已经来过此地,便很安心跟着母亲走,没有多想,现在却依稀回想起来——那脚印许是被烟雾般的风沙湮没了吧?
走进庙里,我和阿妈很快被笼罩进香火燃烧产生的烟雾,有股混杂树皮和干枯杂草的香味。我感到熟悉却不厌烦它的存在。在村落,桦树边角料制成的香是种别样的习俗,阿妈曾经闲聊时提到:“这树在村子种得多,也容易掉皮,孩提时期的她们闲时总要捡些,可以补贴家用,当柴火烧也很好。”
阿妈慢悠悠地把一箩贡品工整地罗列在短桌上:阿奶趁时腌的咸笋,十余只煮好的芋头,几个当季的水果和一卷装的香。坑坑洼洼的桌面像乡下的土路,却不落灰,可以看出有人经常打理这些桌椅。 借着微弱的烛光,阿妈把正徐徐燃烧的香递到我的手上,我跪在佛像前头的软垫上,阿妈在一旁念叨着什么,像“佛祖保佑”一类的话。我在低语声中拜了三拜,接着同往常一样把一小截快燃尽的香插到香炉里灰白的香土里。对此,我早已习以为常,如同血液一刻不停地在身体里奔流,我的故乡里礼佛的人不会觉察半点不妥。
收拾完桌面上的贡品,阿妈看了看外头的太阳讲道:“现在日头还早,我们两个去拜会下方丈吧,你快要开学了,让他看看你今年运势怎样”。 我俩跨进后堂的门槛,两间木头小屋映入眼帘,像是《格列佛游记》描述的小人国。我心头闪过一阵涟漪,想来是对苦修者的钦佩。
我不常到这,眼神很快扫荡起来,顶前面的屋子是烧水做饭的地方,油烟在蓬草画下昏黄的斑痕,小和尚捡的柴火大概受潮了。边头有块菜地,方丈得闲时种些玉米、番薯,都是好养活的物种…… 离方丈住的屋子近了,我突然听见谈话声“你这院快破得不成样子了,该好好地修缮下了”,陌生的声音急促地穿出窗棂,接着缓缓飘出方丈熟悉的嗓音,“这院落是有些旧,但我们俩拾掇拾掇,还是可以住下的”。
我忍不住凑近看,陌生声音的主人是个穿着灰色西装,脸上夹着些许尘土的中年男人,眼神透出精明和狡黠“你这个人啊!就是不愿意别人插手,现在我当了镇长,肯定要帮你这老朋友好好修缮这佛堂,将来这可是我们镇发展旅游文化的重要地点”他讲完话看向窗外,似乎察觉到我这个不速之客,便起身提公文包,朝方丈低语两句就转身走了。出门口时朝我们撇了眼,头也不回地走了。奇异的感觉从身体生发出来,像是做错事被发现时的惊慌失措,调整一番过后,浪涌很快被礁石扑灭。
阿妈敲门,扬高声音对里头说:“方丈啊!我想让您瞧瞧我儿子的学运”过会里头传出句“进来吧”,声音带着些许疲倦。推开门,他在打坐。阿妈脸上升起淡红的云,她对打扰别人不太习惯。方丈没有多说,拉着我手让我坐在一旁,阿妈站在边上紧张的盯着我俩,害怕方丈说出半句不利的话。不久,方丈平淡地说:“安好”,她系在发丝上的心脏才平稳落地,喜悦就把脸庞占据,就向方丈道谢,拉我起身。 片刻后她忍不住问道:“那个穿西装的是谁?来干嘛的呀”,方丈沉默不久,悠悠说:“他是我老朋友,多年前一同在名寺修行。可惜他欲念未除,修行时反生出杂念,就离开了。现在他混得不错,如今当上我们镇长,要修一修这寺院”,她点头,露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寒暄几句就拉着我走,阳光溅进眼眶,我睁不开眼睛了。
但她似乎心情不错,倚着我说:“你小子真有福哈”我点头称是。我发觉我开始质疑,我被石头垫了一脚,可阿妈很高兴地走着,我不再想了……
开学后是秋天,北方原住民来往南方时会不解“这啥子树哟?咋个不黄还不掉叶子”,答案是我学过的气候差异,但我懒得回答。只是接受——入秋后,我们穿着T-shirt,走在碧海间,温煦如夏。中学生活一如山泉,缓缓地流,偶有的几次假期权当石子,投入水中“咕咚”就无影无踪。所以我牢牢记住阿妈的话“佛堂动工啦”“方丈远在老挝的师兄赠送几尊大佛,新筑的,等着过海关呢”返校后还一直回味着,感受舌根涌出思念,我很想家。
下次回家是小年,多数街道比平常热闹,不论南北都是一样的红火。 假期本不多,阿妈还是拉我去看修缮完的佛堂。去的那天我起晚了,吃过早饭就启程,南方冬日暖暖的,我品尝自由的气息,愉快地打了哈欠,快活得像鲁滨逊吃第一口自制的面包。 路原来就不长,走进竹林我突然发现越朝里走越显得宽敞,问过阿妈才知道,原来是镇长命人伐了周围的竹子,拿去卖了权当部分修缮钱。陌生感像烟雾席卷开来,我们沉默地继续走。
佛堂的轮廓透过几支竹子若隐若现,我吃了一惊,急匆匆地朝前去,想要看得更真切些。走到近处,才切实体会到它的震撼——暗红色的大门无言地把佛堂前的尘渣和后头的清静切分。走进去,恍似《桃花源记》记载那般,“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院里头的设施全赶着大佛堂的规格换:不平整的青泥路像修葺花草般铺平,盖上大理石石阶;原本小小个的香炉换作大鼎,鼎身上刻着经文,我猜是劝善乐行,保佑平安一类。我迷了神,阿妈推我说:“这算什么,里面的佛像才好!”期待幻化成浪潮,催促我三步并两步迈上石阶,上面是重修的中堂,小和尚立在门前,见我们来了也不作声,只是点头致意。
具体布局已不需缀述,我一下子就看到那三尊佛像——左尊是骑着青狮的文殊菩萨,右尊是持锡杖的地藏菩萨,中间的自然是如来佛,约是半层楼的高度,都打了层古铜色的腊全都微低着头朝下看,雄壮之感不可言表。正当我流连于中堂,方丈不急不缓地从后堂走出 ,问道:“怎么样啊?”我不假思索地抽离出所有表示赞美的词句,他显得很高兴。
阿妈看向外头,日头大了。扯了扯我的衣角不好意思地说:“得要走了”我无奈地和方丈告别。快出门时方丈叫小和尚扫地,小和尚叹口气,眼神闪过一丝幽怨,进门去了……
随着冬天滋染开来的忧愁突如其来地蔓延到我的臂膀,我懒得离开温暖的床被,苦于要去完成一个又一个维持细胞核活性的动作,我把孤独蜷缩进被子,想哭却又丧失了哭泣的权利,如果阿妈把一切归结为:青春期, 那我似乎也要无话可说了,我相信阿妈的话,会好的……
事实证明这种懒惰的状态维持不久,快过年的时候,我就好起来了。
人人都期盼着有预知未来的本领,那段日子里阿妈好像个蹩脚的预言家——如果我想去外面看看像白马的云朵,她就预测我会遭遇一场冬日里为数不多的阴云。我开始对阿妈有些讨厌了,她总有规矩没有教会我这个读书人,变化很快在日常生活里体现出来,阿妈不开心了。我只好安慰自己是青春期的副作用。
自然地,我们还要一起去镇上置备年货。冬日里的天空大多都安装雨刮器,我套上很久前买的马褂,外头不冷,弥漫着暖融融的烟火气。跟在阿妈后头,我没有注意到她在和摆摊的人斗嘴,一群大妈之间聊的无非是柴米油盐一类的事。 扭过头,我注意到沿路的墙上贴了不少的传单。我凑近去,悄咪咪撕下一张,上头没有什么痕迹,是近期才贴上去的。看了一会,我才明白原来是宣传村里的寺庙的,小小的一张却铺满发展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作用,只有最后寥寥几行点明了是我们的寺庙,我对密密麻麻的像蚂蚁的字体有些作呕,却又高兴于这件事,我们村似乎要被人们记住了!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过年当然算作是我的快乐,我在年关里头大吃大喝,肉啊鱼啊和流淌在血液里的茶水,遇见的每个人都健谈起来,直到我在夜晚里闭上双眼,这些都像美梦一样被压在夜里,第二天又是另一番光景。
“庙里出事了!小和尚,方丈和新来的镇长都被抓了”阿妈脸上渗透出一层层阴云,仿佛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我们心头。 “真的假的?”我的音量一下子拔高了,我看着阿妈垂头丧气地点了点头。
“还记得那几尊缅甸来的大佛吗?”阿妈问。我点点头,心里头想到了什么不好的东西。“怎么了?”我不解地问,不就是几尊大佛嘛!为什么方丈们会被抓呢?
阿妈的叹息中带着怨恨,不安地说:“里头装着白粉,整整三个佛身”我的下巴突然合不上了,被人掰开来一样僵硬。我脑袋嗡一下地播放起嘈杂乱码,不断地摇头,想要否认这件事的发生。寺庙和我的连结仿佛在一刹那断裂,我想起和方丈的话谈,不可置信他们会做出这样的坏事。 一时间我们都愣着沉默,直到我鼓起勇气问她:“是谁做的,又怎么被发现的?”阿妈的身体微微颤了起来,眼底流露出迷茫和痛苦。
“听去的人说,小和尚起了贪心,他对修行生活早就腻了,就和见利起意的镇长还有方丈的师兄从老挝走私了一批白粉,包装成佛像送过来。那镇长鼠目寸光,向方圆十几里的人宣传起这几尊大佛,以为让庙里热热闹闹的就能掩人耳目。结果那庙里一下子挤了太多慕名而来的游客,个个都在点香,好像个大火炉一样烤着佛像。几个眼尖的就发现不对劲了,佛像都升腾起白色的烟气,靠的近的都头晕起来,这事闹得很大,引得警察来调查,才发现是白粉。”阿妈的话直戳戳地捅进我的心底。
我们的家要“出名”了,被遗落的南方村落会以让人羞愧的模样登上历史的荧幕,那么有我就是证人,有阿妈是被牵着鼻子走的旁观者,有方丈是牺牲的求道者,像是一场未经导演的舞台剧。
我选择离开,阿妈也不信佛了。
云的衣角被烟裹着,我却再也闻不到桦树边角升腾起的香气了……

 |

 |

 |
范德清 |
张利利 |
汪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