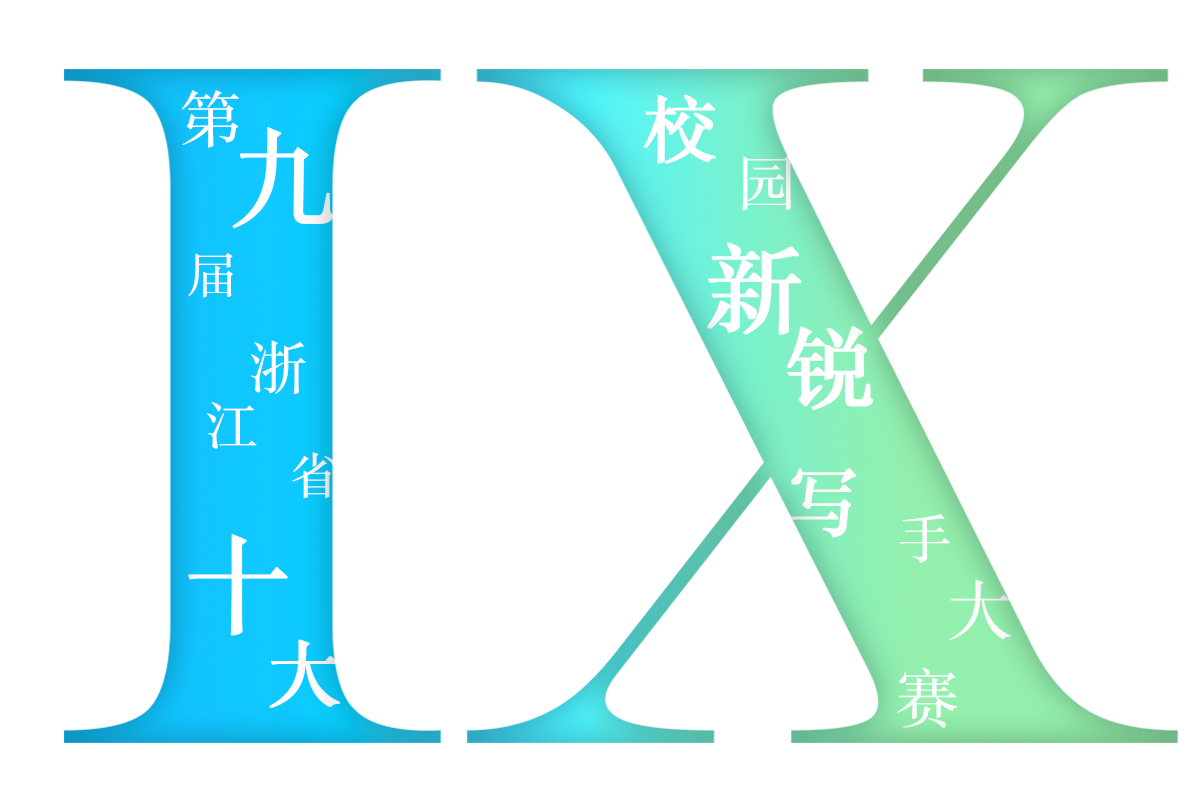聋
知邬 发表于 2022-07-31 21:21:25 阅读次数: 34289
她们本都理应飞翔,在空中歌唱自己所爱所想。
-
感官对于任何生物而言都尤为重要,当然还有无数数不清的重要东西无法舍弃,可最终的选择权总是不在自己手上。
我睁开眼。
拥有过或从未拥有过的一切和我都是过往,在面前安静沉寂空无一人的景象中显得不真实。尖利刺耳的吼叫吵闹、属于人类的哭声呐喊、物品物件相碰撞炸开裂碎流落叮当……全都散去了。那些记忆也许不是我的,我浑身只是亮丽淡淡映光的黄色羽毛——即使此刻因泥泞灰尘望不见原本,但那些混乱不堪的记忆怎会是属于我。
感觉却真实地触手可及,伴随着破碎凌乱的画面能听见的声嘶力竭。戴着皮手套的中年男子总会拎起我的脖子或逗弄,企图令我发出一丁半点的声音,我终究抵不过而妥协放歌,那时我发现我已然听不见任何外界,哪怕是自己。
于是我被抛弃……被人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都会被抛弃,我有什么地方可去,我无处可去,我漫无目的地飞、飞,却飞不动了,双翅因过久施展不开也渐渐失去力量,也许以价值评定我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任何剩余。我从树枝向上,我凝一口气力挥动、拼尽全力向上——
砰。
应该是以这种声音的,我撞上一扇窗。
被救助属实是我的幸运,可警惕必不可少,没有谁能确定在遇到事情的第一时间就评定它究竟是另有所图或是面临的光辉前路,但至少此时这让我免于横尸郊野。
她的行为逐渐获取我的信任,足以安全的小空间里,而后每次为我填食瘦肉条,许久未吃过如此丰盛食物,逐渐逐渐,我与她亲昵起来。
她定是没有坏心思的,总爱把我放在窗边,一头的窗外斜支的电线杆年久失修,不久便能见电光在深色电缆见一闪而过,她把我挪得离那远很多。偶尔试图伸出单只手指捋我的毛发——自然让了。我的羽毛也因她细心擦洗而重归了原本亮色。
我见她的嘴唇一张一合,听不见什么音节从嘴中传出,这话说得可笑,像是我听得见就听得懂那样。
我是不是聋了?这很不可思议。
确实,我许久没见听过声音,到这里之前我在细铁丝铸造的简陋肮脏牢笼内,人来车往鸡鸣狗吠,渐渐地外界喧闹声都变得淡,似菜农冲洗蔬果上的泥土一遍一遍之后留下的水从泥土的本色变回清列的,水本身的色泽那样淡。我有歌喉,我自然有,我有着曾在山林间最明亮透彻的乐曲和颂章,可我许久未曾开口,我不知它是否如旧,我亦不知我的耳朵何时在这闹市中悄悄失去了功能。
可他们总说,你想表达时,你要多听然后出声……
听不见至少还能看,可一但要来人,她就把我偷偷藏进深柜子的小小角落,巨大柜门遮挡住宽泛的视线,只有那一线光可窥见。
我窥见长相如同生肉堆积起来的男性立在黑暗里,火星燃着的烟头冒着热意往女孩儿鲜嫩的皮肉上硬戳留痕,烟灰轻缓落到地上为线织地毯添洞。我窥见各种利器钝器从高处向她砸下后低低反弹起的弧度。我窥见她伸长胳膊去抵抗,在空中挥舞试图抓住一根稻草似地猛力,胡乱蹬向外的双腿。
我窥见她哭喊,她挣扎,她用尽全力向其他人求救,其他的姑娘。可刚有挺着孕肚的笨拙往前就被拦下,另的人扭着身姿去拽她乌黑亮丽长发,缝隙被重重人影挡上……
人尽数散去后,她伸出布满伤口的手臂,轻轻颤颤用手指缓缓顺着我羽毛而过,一下一下,遍体鳞伤的痛啊,在我面前却像是安宁了,可她红透的眼眶鼻头耳廓,她浮肿的眼皮厚重地遮掩原本美丽的眼珠,她因为过度激动而仍微不自觉颤动的肢体,我都感受得到,清清楚楚。
我想表达时,我听不见之后出声……
我终于决定开口。
我竭力地唱,撕心裂肺扯出明亮绮丽的嗓音至少我认为它会是,它曾经确实如此,但如今不同。久无清润朝露顺我喉管轻滑而落,久无同伴欢歌引我徜徉恣肆,久无阳光——明媚刺目却能暖得袭裹着任何一具身躯,只要在他看得见的地方……只要他、他看得见。
他看不见这里,否则怎会终日不见。阴暗的地方总是充斥食物的稀缺与硬生生沁入骨头中的寒冷、痛苦与绝望。
他是瞎了吗?如同我聋了那般悲惨地失去了对自己或是对他人都多多少少有些许意义的感官,谁都是不幸的。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聋了,自然亦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瞎了,可至少,他不往这边瞧,瞧上哪怕一眼。
我想此刻我的歌喉也许不能称之为歌喉,它大抵和我曾多见过那些浑身深紫色的家伙所发出的声响一样,嗓子被人用冒着点点火星的烟头硬生生烫开破洞似得,缩脖子再用力向上向外撑开扯着羽毛也片片微张开距离,露出零星同样肮脏的皮,从千疮百孔钻出来的皆是破碎凄厉尖锐划破了一切阻碍直冲入皮肉里搅得血肉模糊……好在我大概是再也不用听到那种噪音,我也听不见我的,也许听不见在此刻倒显得成了一种恩惠。也许不那么难听,因为——她笑了。
我侧头正看她,第一次见到那样的表情,起初我以为自己难听亦是因为她的眉头团了起,眼睛却仍盯向我,嘴唇微张,张却未合,应是没在说话。片刻过去她面上舒展开来,敛下眉眼,嘴角向外抽二三下,嘴唇也是微颤着,脸上皮肉被牵扯木纳地舒张、舒张,再向上……
很艰难地,很缓慢地,绽开一个笑。
冲我。
原来她笑起来那样好看,那双眼里是又充上了泪吗,蒙上一层雾般得我看不真切,却又亮晶晶地透着光,哪来的光呢。她心底的吗,或单是我眼中的。
翻不出句子形容,我本就是渺小的卑微生物,我的脑子能思索这么多已然是超乎常理,绝无可能的事情,可一切都早已超乎了,比如说我此刻的存在和她们的遭遇,也许我的乱想是源自于我这本就蹊跷降临的灵魂而不是来源于肉身拥有的小不大点脑子。
对,我这蹊跷的灵魂……我与她的这抹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如同是,如同是,我见过的,不是在别人脸上也不是在梦里,而是真切地,她笑着。好似前生,也许,我有过的前生。
她用她同样许久生疏的笑容回馈我稀烂的曲调。
我是不是聋了?我复问自己,我觉得、我记得,她笑的时候伴随着肩膀的上下微颤,那时是她笑出声,清亮地更甚,且柔软地化开了心,真蹊跷,我长时间应是从未听到任何声音,此时却好似听见了她的笑,天降甘霖。
之后的日子是仍与之前一样,她被迫做那些不愿意做的,却抵抗地少了,她仍是不甘的却因毒打和食物而屈服,她给我许多许多肉条和果子,见我啄食下咽,我的情况慢慢好转,她总是开窗似是想放我归去。
我偶尔唱两声与她,我想我听不见可她还能够,我不能多再去伤她的耳朵。我愈加想听她同我讲话的声音,但旁人,都好似什么也听不见。
她又打开窗,神情不同往常地深沉不舍,这次我必须该走了。
那些哭喊求救的声音呢?那形单影只却爆发出洪水般席卷所有的不甘与痛楚的呐喊呢?那些抵抗试图打破囚笼获得本应拥有的自由和光明燃烧自己而发出的嘶吼呢?
震耳欲聋……震耳欲聋!
我是不是聋了?我是聋了,可聋的不只是我,那些千千万万本应伸出的援手,那千千万万本应打开窗子让太阳的目光落向此地的人,他们的耳朵呢,被人捂上或是视若无睹挡了捂别人耳朵的人。
她们的声音那样响亮,那样凄厉,那样令人痛心,却无一例外地,被层层叠叠厚实黑塑料胶布贴上嘴。那层壁垒太厚,说不出,说出来亦无人听得见,他们甚至……甚至以此为乐吗?
她站在窗前仰望浅得漂洗过无数次的蓝色天空。不远处的窗台上仍是那抽着烟的男人,面目在距离阻碍下看不真切却只觉得反胃,烟雾飘飘散去,如同无形的罪恶。
飞吧。飞吧……
边上电线杆上电缆仍偶然冒出一两下电光,我回头看那树荫里的楼,分明是艳丽绯红的一座牢狱,困成一处阴暗角落,而窗外明明有光,有那样明媚的金光色暖光。我从窗口逃脱,这是第几次逃脱。
那阴暗处的男人貌似发现,仰头盯上楼与楼一线缝隙。
-
渐金黄色羽毛从半空中飘落,落回姑娘紧锁的前窗。

87

86

88

86

85

88

89

79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