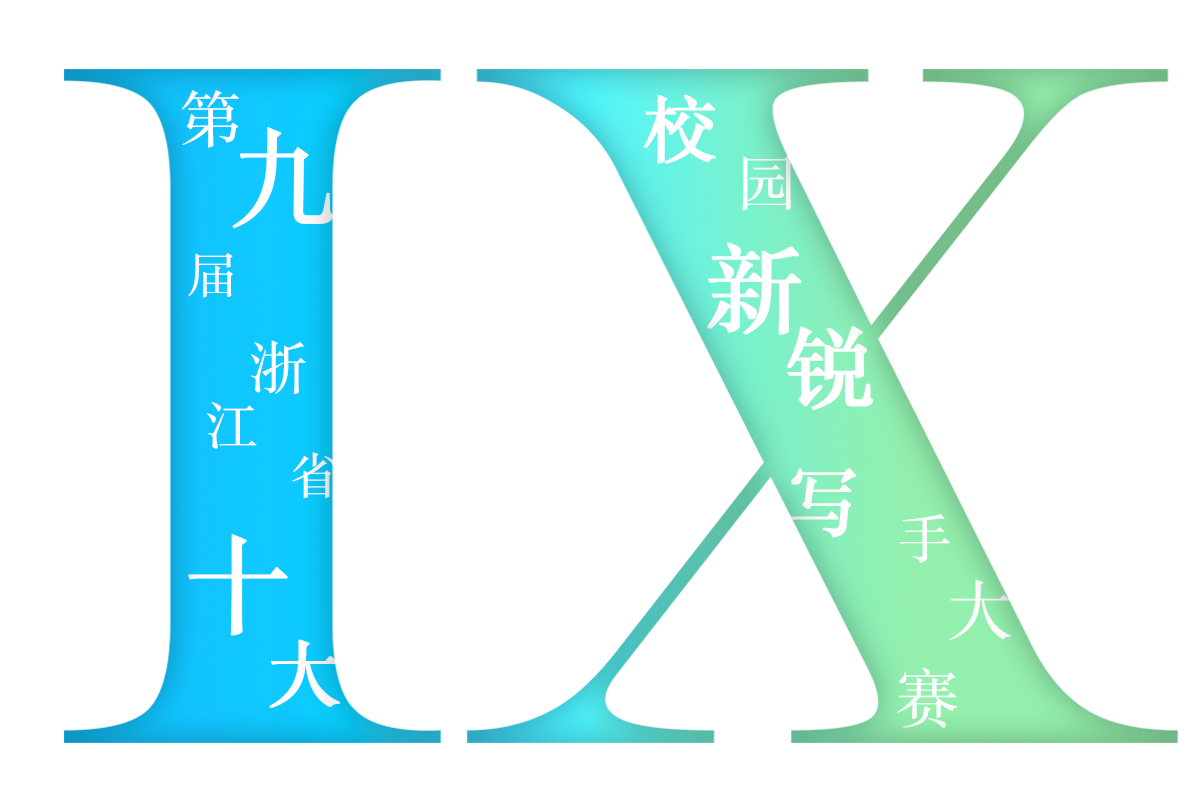小金儿
joan 发表于 2024-05-01 21:30:25 阅读次数: 5121985年秋的时候,我刚从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便听从老师的引荐,乘了火车从台北到潮汕。
路上人挤着人,团着大袄坐在铁座上,身旁拧着眉拿着电话嚷着忽地啐一口浓痰,飞溅的沫浅沾上了铁皮墙,黏稠地慢慢滚下。一小孩往我身上挤推着,许是无位,便可劲被推在我身上,车箱上中呼出的一口热气也操着掺着腥臭味,团巴团巴地揉进了鼻孔里。
父亲曾带我来过,看着窗外缓缓而过的的树木,内心不由起了如那时般欣喜的心情。刚从火车下站时,车鸣噏嗡地响在耳边。
整个车站人推着人人挤着人,我眼前一个个剃得青白的头在晃着,我犹是看见火红的星子一颗颗砸下来,在空气中冒了火,纷纷点着了整个车站。
“李先生!李先生!”我耳边传来一声声叫喊,一个大体十五六岁的姑娘跑到我前头。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白嫩嫩的脸上糊着一块红一块白,汗水湿了发粘在了头上,她不在意地拨了下脸前挡住的头发,脸上泛着红晕气喘虚虚地呼唤着我。
“欸!”“你好!你是青莺剧团来接我的吗”我有点激动,期待地看着她。
“是的,李先生!我是青莺师傅的小徒金儿”
我点了点头,跟着她左绕绕右绕绕,竟如个泥蚯一般从熙攘的人群里滑了出去。我紧跟着她、恐怕落后,汗圆溜溜地滑下额间,也来不及拭下。
左右总算绕出了人群,我急切地大口吸气,想闻闻这大陆的空气与台北的空气有何不同,来不及慢慢品味,小金儿一把拉住我向前走去。
"呦,小金儿回来哝!”刚下车便听见院门口的妇人冲我们喊道。"细啊,阿嘛!我带李先生回来了,锅里还有饭吗?"小金儿边走进门边说。
"有,在锅里还蒸了两片肉就等你们来了!"李先生,你好!我是这的青莺师傅请来做做饭扫扫地的,啊!对,你喊我成姨就行了。"成姨嘿嘿地笑,额间的纹挤成了一团,仿若皱巴的布头在我眼前晃着,我于是点了点头喊了声成姨,便跟金儿食去了。
“嗐!成姨竟真舍得煮了这肉了,我还以为她说笑呢!”金儿打开盖子,欣喜地嚷道,随后从旁拿起两个碗,一个印着“青空万里”一个印着“莺飞燕长。
我把饭舀好,两片肉,一片盖在我碗上一片盖在她那儿,油滋滋的肉片还冒着热气,氤氲在我俩之间。忽得她噗嗤一笑,尖着嗓子叫着"李先生、李先生,这下我可看不清你脸了,哈哈!”她笑得两叶柳眉弯弯的,我也被她感染了,心里止不住觉着好笑。
小金儿虽然爱闹,做事却一点也不含糊,让我歇息着,晚上再去看她们的戏。我左看看右看看,心想我这也便是来了啊,止不住内心有些迷惘。
休整罢,我走出门,天色有些阴沉,星子被一颗颗重新挂上了天幕,那一颗闪得最亮的该是刚从火车站拾回来的吧,它们也许刚洗过澡,刚游过顾子江呢。
土路上没人,我从院门出去看见一块块的石板走上了街。吼!原来人都在这了。突然人流越来越密,像金色的麦浪,被风一吹,向前涌着,勾着层层波浪,一层层的。我被推着向前,竟莫名到了一个大广场,前面有个大戏台,粗工制成的布被风缠着,似是跳了曲霸王与别姬。
“吼了,卖答辽”我听前见前方传出一声吼,人群慢慢地如波浪般静了下来,被感染着,我也忍不住屏住呼吸,用目光试探着台前那块红幕。似是感觉到了什么,身前的大爷眯着眼叫着“青莺师傅,青莺师傅!“大家也纷纷向着那处看去,边鼓起了掌。孩子们从缝隙中钻过,眼中亮着光,兴冲冲地往那处瞧去,一片望去,皆是盛情,一耳听之,皆是掌声。
此处盛景,这般热闹,是我在台北生活学习的二十多年中从未看到、听到过的,也深深地震撼到了我的心,使之不由地鼓动起来。
太子青抱着婉儿一同沉入冰冷的湖水中,凄冽的尖叫撕破了天空,直入云宵。忽得轰隆一声,雨水哗的打在我的脸上,整个人仿若从梦境中惊醒,浑身冰凉,周围的人声顿时喧闹了起来,孩子迷茫地眨了眨眼,似乎是被婉儿最后那声惨无人寰,不甘绝望的呼救吓着了。
“呼!青莺师傅厉害啊!连降雨的神仙也被青莺师傅感动了啊!”愣了片刻,不知谁大声喊着。是啊是啊!众人连忙跟着说道,不知谁带起了头,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似是在夸耀这场戏又或是在感恩这场雨,总之,那夜的天空仿佛被热烈的掌声,赤诚的心所顶破,最后落出了一痕裂缝,光剑生生地从无数裂痕中刺出,疼得我的眼睛生生的流出了泪。
待到第二日时,叫卖声,鸣铃声,敲门声齐在屋里屋外响起,我眯着眼打开了门。洗净食罢,再次走上石板路,轻踏着上了街。昨日的狂欢像是场艳梦;是林中的仙子诱着人前进?是聊斋中的狐仙媚眼如丝?我恍若空空一梦,南柯梦中,早已羽化成蝶。
“李先生!李先生!你可让我好找,快去吃茶罢!青莺师傅等着你呢!”金儿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转身一看,果真见是她。我点了点头,与她一同去见了青莺师傅,内心暗自有些紧张。说起来,青莺师傅早些年曾与我父亲有过联系,自我父亲去了后,便也少走动了。
到了堂屋,遥遥便望见青姨坐在椅子上,只身穿了件淡白裙子,上面绣了两朵牡丹花,盘了个发。看见我来了她露了一抹笑,忙站起身来迎我。她断断续续同我讲着,小金儿倒了茶,坐在一旁昏昏欲睡,日头上移,整个大火球越发亮越发剌眼,她还在说着:“你父亲…”青莺师傅紧张地看着我,她一言不发定定地看我,我害怕地恐惧地与她两两相望。
她的眼神像极了父亲临别时见我的样子,我想起了父亲临别前躺在病床上,两只眼被糊住了眼屎,只眯出一条缝就那般瞧我,他怨毒般看我,似是要把我一同拖入地下阎罗殿好细数我的不是。
许久,她站起身走出了堂屋,小金儿也站起了身,冲我说道“李先生!走罢,不然该饿了!”她那清亮的嗓音将我从混沌中拉出,站起身走出门去,正午的热风一烘才发觉满背湿透。
日光直射地面,我抬头冲最亮最热的那处望去,不一会儿眼睛痛得像在跳,浑身的冰凉这才被暖透。
酒足饭饱后,小金儿邀我一同去晚上作戏的空地参观,我欣然而去。我们一同沿着石板路走着,轻风拢起了她耳边的发丝。她一路叽叽喳喳的,在快走进空地时慢慢安静了下来,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空中一点,蓝白的天空,分明整洁,那一点却似女娲补天时忘记的裂缝,被遗忘着,只剩它孤独地看向地面。
戏台很简单,两边挂了两块木板,一边写着“青莺剧团”一边刻着“敬请观赏”,台前的幕布还没升起,红彤彤地衬着金儿的脸也似抹了红膏。
“李先生!这边,我带你看看戏团的“秘密”!金儿向后走着,向我摆了摆手,倩笑着。
“金儿!你怎地来这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边抹着唇膏边信步走来。她翘了翘嘴角,弯了弯眉,一双眼带着媚,眼角微红勾着细长的眼线小脸紧致微圆,嘴巴红嘟嘟的,俏丽中带着媚,却又媚而不俗。小金儿转头把我拉上了后台笑嘻嘻地对秋信说:“好秋信,我带了客人,师傅吩咐过的你可得好好招待他!”说罢攀着秋信领我走。
我跟着她走向了台后,看戏的人看是台前畅快淋漓的愁苦,豪情万里的辽阔,悲凄凄,惨恨恨的爱情,戏后的人来往于妆台,换衣棚。经久不绝,长久如此。
天气越发冷了,南方不下雪但湿冷的快冻掉手脚了。青莺师傅裹上了厚厚的毛绒袄,小金儿的脸也冻红了。不知怎地青莺师傅咳嗽越发厉害,这也让大院新年的喜悦少了许多,总有着一丝忧虑。小金儿这几天一直看顾着青莺师傅睡,恍恍惚惚的。
早晨我披上大袄走出门去,一堵冰墙拍面而来,脸上也挂上了水珠。忙拢了拢衣服,哈着热气,心中却升起一阵子不详之感。南方的冬天树木理应依旧青绿,但不过一夜一棵常青树满头白叶,在风中哗哗作响,忽地,小金儿从远处跑来,铁青着脸,美目中盈着泪,嗓子粗粗地恳求我:“李先生!您认识什么好的西医吗?师傅咳血了!”我惊住了,昨天不是好些了吗?怎的,怎的,如此……
我赶忙去找医生,却无果,这大过年的又哪来的西医,我们都晓得,但却没人愿意说出来,因为那是那个冷的剌骨的早晨唯一的慰藉和希望。
不过两日,青莺师傅便去了。她临别时喊我到床前,一言不发只看着我。那眼神就如当初父亲瞧我的一般,慢慢的她的眼睛失去了焦点。她躺在这个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躺在这个顶破旧的账子里;她的眼眶发黑深陷,皮肤粗糙,十指的指甲长长的,里面藏住了污垢,就这样死去了。
傍晚,我们雇来抬棺的人也来了,他们一步步抬上山,我们步步跟着,到了山上,把棺一下,也就真正天人永隔了。小金儿扑通一下跪下,弓着背哭嚎着,一声声愈来愈惨烈,一声声愈来愈悲恨;像是幼狼在死去的母狼身前呜咽,最后什么也说不出,只能从嗓子眼吐出泣血的痛苦。在橙红的天幕下,太阳西移,她弓着背突起,仿佛一个坟包,融进了山头。
成姨什么也没说,只衰衰凄凄地拭着泪,我看着红澄澄的天色,心中升起一股悲凄,我担忧着青莺剧团明日光景,担忧着小金儿。
小金儿回去后在院中散着步,突然跑到厨房拿起扫帚在院子里扫着,细细地,慢慢地扫着尘灰,厚厚的衣服束着她笨拙地摆动。
今年春天似乎格外漫长,小金儿承了青莺师傅的冠,日日忙的脚沾地,我整日见不到她,只能在晚上看戏时遥遥望一眼。她戴着青莺师傅的冠,化着红妆,卷着假发,细细的嗓音宛转悠扬,长长地传到顾子江,长长吹到了城里,吹到了成姨的耳朵里……
夏天快要来了,从春天开始我就爱上去镇上的留仙洞坐上半日。点上小杯番石榴汁和一小块薯饼从下午坐到晚上。我白天在留仙洞待着,到了晚上又匆匆赶去小金儿那。自青莺师傅死去后,一日日见着人群攒动到稀稀拉拉,又从三三两两目睹了空空无人;我一刻都不敢再待在那,一刻无法都不为青莺剧团感到悲切。
我开始躲着她,她那眼睛只一瞧便像极了曾经的青莺师傅,那眼看着我时仿佛在焚烧我的身体痛得在地上打滚,痛得在地上打滚,痛得眼红了,白色的眼珠爬上了红血丝,嘴唇上哗哗得掉皮…痛得…我不得不躲着她。
远远地隐隐地看见她房中亮着一盏灯,窗里显的身影正坐在窗前,面前摆了顶大冠,我见过几次,绝对错不了!是青莺师傅的冠!
忽地灯,灭了。我抓紧的心也一块儿松了。
大院的门每日都有人出去,都有人不再回来。
中秋节我们聚在一起吃了顿饭,我、秋信、小金儿一人一碗,还有一碗是给青莺的。大家没什么可说的,也就感叹下今朝,便匆匆收拾完了,秋信独自一人拿着手电在小巷中向外走出,小巷里一片死寂,乌黑得不见光亮,令人心慌。
倏地秋信打开手电,光亮洒向巷口,在黑夜里吞噬了黑的死寂,独自一人亮堂堂地,抬着下巴,直板着背向前走去。我心中隐隐有一种感觉——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她了。
送完她,我转头回院了,屋内小金儿点了盏灯拿着刀片一点一点地削着手上的死皮与茧,薄薄地一层又一层慢慢离开了她。灯光照在她半边脸上,像印了个黄澄澄的胎记,笼罩着她的黑眼珠,荡出了光纹。
她终于病倒了。我早晨见她许久未出便进去寻她,一进去便吓了一跳。她僵直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得如僵尸,眼周赤红肿胀地围着中间的眼球,两颗黑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我,嘴唇上粘着一片片皮,唇纹裂成了痕,两个唇角边黑红黑红的,似乎藏满了污垢。我急忙跑去喊她,生怕她一闭便再也醒不来了,那时,我恍若在青莺师傅死去的那天。
该是我的错觉,她喝了药第二天就差不多好了,全然不见前一日的痛苦,但我心中仍惊慌着。
病了一场,金儿似是想通了什么,和戏班的演员们商量了些什么,又在晚上静静地把我拉在一旁,面色认真地对我说:“李先生,我和他们商量过了,一部分人仍留在这,一部分人愿意与我一起去北京唱戏,我留在这没有出路的,只有北上才能打响名声。”说罢她似是口渴了,低头喝了口茶继续说道:“我也无法子了,只有这样,师傅留下的剧团才有一丝生机。”“我也无法了,只有这样……只有啊……”她独自喃喃道。
这几日我一直心口不平,此时也不知是好是坏,也无法,这不是由我来决定的。她的眼睛看着我,我知她是想留下我的,可我悲哀地认识到我终究只是个局外人。
又一个夏天了,自去潮汕后我已记不清是第几个夏天了,在第一个夏天时,我去到了那,在第三个时,小金儿离开了那,第四个临近时,我也背上包袱,扫了一天地,再把大院细细看一遍,关上门,别了这四年光阴,别了这春去秋来,别了此番光景。
终篇
二十年前的事我早已模糊了,那时车站的汗味,秋日的绿叶,浮池的水藻,小金儿铃铛般叮零的声音,我都快忘了……
那几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我以为的春去秋来也不过是叶子缝隙中窥探的半瞬。我细细地摸着空气中的暖流,四年的时间,我与小金儿,与成姨,与青莺师傅竟一张照片也未留下,无可怀念,只剩那缓慢逝去的记忆,可不时揪出来查看一番。笔至于此,心中怅然,几十年光景过去,倒成了寻寻觅觅。我似是做了个梦,回到了太子青的那场戏,婉儿凄婉的叫声恍若刺破了耳膜,眼前又是一场热闹。

 |

 |

 |
范德清 |
张利利 |
汪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