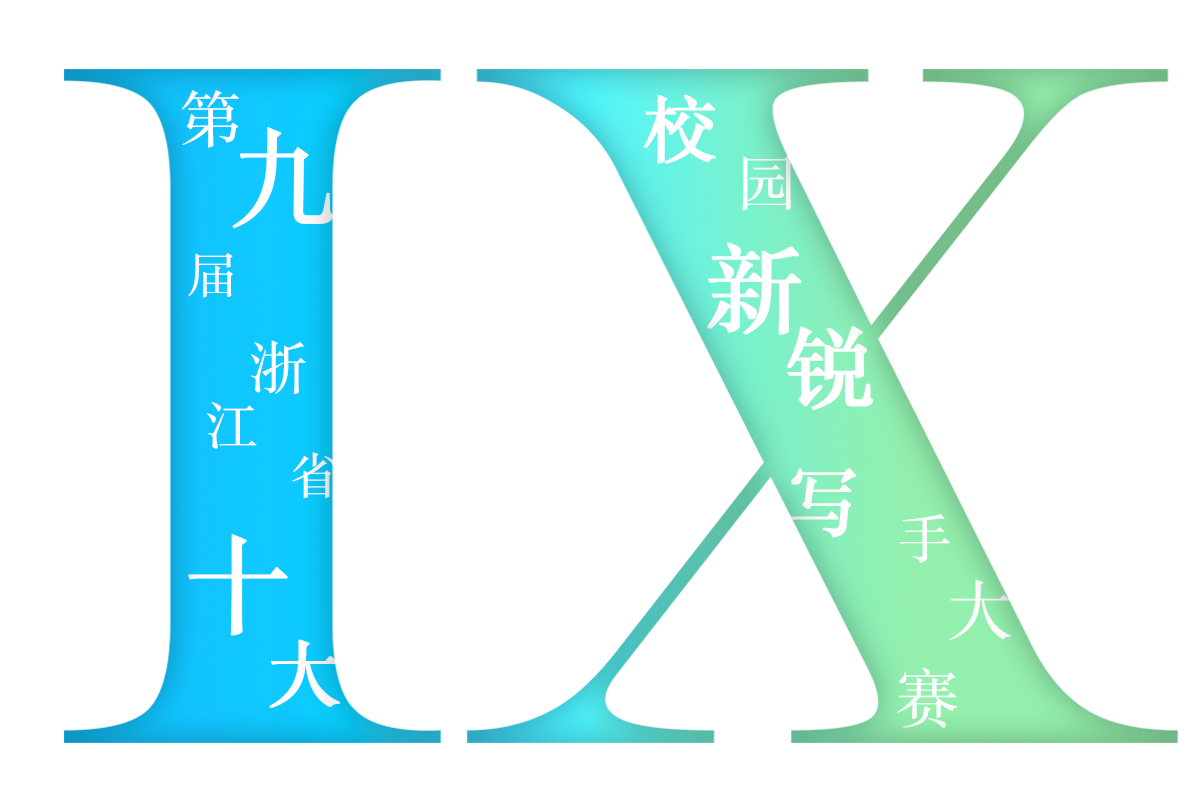长恨歌
Spril 发表于 2022-06-30 21:36:58 阅读次数: 1492夤夜,宫灯已经燃尽了,迟迟无人续上。
黄昏时分下了一场小雨,阶前的梧桐叶积了一地,重重叠叠,倒映着明净的月光。晚风吹拂着院中的草木,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不知从哪儿传来促织的鸣叫,一声高,一声低,此起彼伏。
又一阵穿堂风过,吹得他不由得拢紧了氅衣。
入秋了啊。
他忽地又想起了很多年前,在东宫的偏殿中度过的无数个这样的夜晚。
一样无边的寂寥,冷清。
1
年岁渐长之后,他早已记不清母亲的模样,只记得那是一个温婉和顺的女人,宫中上下对她都甚为敬重。
——后来他才明白,其实不过是因为父亲的缘故。
他父亲的偏院中有很多像他母亲这样的女人,年岁久了,她们连名字都被忘却了。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年复一年地守在宫殿的一隅,期盼着一个于她们而言仅是名字的男人的恩嬖。韶颜稚齿,但如宫中的丹若花,芳菲转瞬即逝。开时明艳动人,风雨飘摇之后,也无非残枝落叶。
或许是因为母家的势力,或许是因为他的缘故,他记忆中的母亲总是一副淡然的模样——有没有恩宠对于她来说,都是不要紧的。
母亲如同常青竹一般安守在她的别苑中。很多年后他才隐隐想到,或许母亲才是这九重宫阙里最懂得深藏城府的那个人。她小心翼翼地权衡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如履薄冰地为她的丈夫和儿子下出每一步棋。她布的这盘棋是何其精妙,以至于将自己也至于绝境。
长寿二年的新年,母亲最后一次掩上了他的房门。
那年春天,庭中的竹子开花了,鹅黄色的花穗沉甸甸地低垂着。不过半月,栽培了多年的竹林便都凋零。宫人引为怪谈。
很多年之后,看着上苑的竹色,他仍然在想,那个如明竹一般的女子,在面临死亡时,是否还保持着她一贯的得体?她是否有过片刻的懊悔抑或愤恨?她是否想到过宫墙之外她懵懵懂懂的孩子?
他还有许多的疑惑,可惜都问不出口了。
2
在跨出那扇东宫朱门之前,他已经在门内幽禁了七年。
七年,他至今为止一半的人生,都是在这座狭促的宫殿中度过的。
宫门被开启的那一刻,正如七年前宫门在他眼前缓缓合上时一样的壮观。
他终于见到了久违的宫墙。朱红色映得他的素衣愈发苍白。他险些跪倒在地上。
他想起最初被幽闭的日子里,任凭他如何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宫门始终对他紧闭。后来,他哭累了,便在母亲怀中昏昏沉沉地睡去。待到他醒来时,母亲不知从何处捉了一只鹊儿,装在一个精巧的鸟笼里,来哄他欢心。
那是一只红嘴蓝鹊,羽毛光洁如紫玉,翘着长长的尾羽蹦来蹦去,模样笨拙,叫声却婉转动听。他给它取名“玉”,从此爱不释手,时时将鸟笼带在身边。他吟唱,阿玉便也应和着啼啭;阿玉在笼中翩跹,他便提笔作画。
他从未想过长久,直至那日父亲呵责他“玩物丧志”,又怪罪母亲对他太过放纵。年方五岁的他惴惴不安地垂手立在一旁。他未曾想到往日温厚谦和的父亲会流露出如此狰狞的神情,更没有想到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竟是那样的不堪一击。他恍然意识到父亲早已不是往日的父亲了。纷至沓来的变故破碎他们彼此相依为命,却也使他们间本就脆弱的的关系愈发支离破碎。
平日里相敬如宾的夫妇,此刻一个大声呵责,盛气凌人,另一个唯唯诺诺,诚惶诚恐。
——他早该明白的。
父亲对母亲或许有几分真情,但那份感情实在是过于凉薄;母亲或许也并不爱父亲。她对父亲更多的是依赖,是敬重。她可以与他举案齐眉,同床共枕,但绝不可能张敞画眉,琴瑟和鸣。当她滴水不漏地应对着父亲的问话时,眼底的淡漠就像是波澜不惊的潭水;而父亲亦以他久处东宫的威严,居高临下地断定着母亲的臧否。
他默不作声地将鸟笼收了起来,交给了管事的宫人。从此他潜心策论,凡事周全,可父亲再没来过。
“蛊厌”之事后,他从宫人们模棱两可的私语中猜到了事情的轮廓。
他应该相信吗?相信他的母亲会是那般阴毒之人,还是相信母亲会就这样离自己而去?
他推开宫人,奋不顾身地向偏殿跑去。
母亲告诉过他,鹊儿是最有灵性的。青鸾舞镜,杜宇春心。它通晓人的心情,所以悲伤的时候听它的叫声,亦然是悲怆的——但是,哪怕是啼血的歌声也好,至少他在深宫的每一个漫漫长夜,都不必再孤苦伶仃。
他疯了般寻找阿玉的身影。
——可是,阿玉死了。
负责照看它的宫人伏在地上,哆哆嗦嗦地告诉他,阿玉是自己一头撞在鸟笼上,撞死的。
他愣了片刻,往后退了半步,再半步。
他不吵不闹,克制着自己不去看它,正如他没能看到母亲最后一眼。
他独自一个人蜷缩在纱窗下,明晃晃的日光透过窗棂落在他的脚边。
他想起曾经度过的每一个夏夜,殿外烛火长明,风吹影动。他坐在桌前,捧着书卷昏昏欲睡。母亲在一旁替他轻摇团扇,或者点上一炉熏香,柔声唤着他的名字。鸱鸮在宫墙外低低地啼叫。
后来,母亲走了。鸱鸮不叫了。阿玉来了又走。最后只剩下他了。
月凉如水,母亲曾用过的铜镜此刻泛着幽幽的光,逐渐浮出一张陌生的面孔。
他跪在镜前,久久凝望,忽然想起那只在镜中起舞的青鸾。它在镜中看见了什么呢?是同类,还是孤独?
殿内万籁俱寂,风吹过竹林簌簌作响。
他解开外襟,在大殿里跣足而舞,冰凉的触感从脚尖到全身,衣摆随之旋转,仿佛一只不受拘束的兰雀。此刻的他,只想飞出宫阙。
3
亲眼见证那一场宫廷政变时,他方弱冠。
他看着平日张扬跋扈的两人,衣衫不整,神色恓惶,如同铩羽之鸟,被斩于军刃下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地面对死亡。
他经历过不止一场生离死别,却都没有眼前的使他感到触目惊心。
在不情愿的咒骂、呻吟声中,那对曾风光半世的兄弟倒在了血泊里,残留着余温的鲜血溅到了他的脸上。一股腥味弥漫他在的鼻尖。
他抬手揩去,鲜红色的,像是丹若花的颜色。
原来死亡也是这么一件身不由己的事情。如果是他的话,绝不会动刀的。
三尺白绫,或许更成体统吧?让他们体面地死去,亦不必玷污了这大殿。
风平浪静之后,一切都会重归正轨。始作俑者或将名垂青史,或将遗臭万年,唯独这青砖黛瓦,将长久地存在着。
他将手上的血迹在剑鞘上蹭干净,跟随着众人向殿内走去。
他见到他的祖母,当今陛下,一如往日的威仪庄严,质问道:
“乱者谁也?”她的声音里还带着些强行克制的颤抖。
“张易之、昌守称兵宫禁,罪当万死!臣等奉太子诛贼臣。天意民心,久思李氏。愿陛下传位太子,以应天时!”
陛下一怔,身子如同风中的枯槐,几近不稳。
曾经最信任的人,此刻都站在了她的对立面——她也曾不可一世,但终归还是败了。
他看着她,一步步从那九五至尊的位置上退下来。
她头上的鎏金步摇战栗着,华服亦显得有些沉重。
他记得自己上一次见她时,她还是一个倨傲而寡言的妇人。她将他召至跟前,端详良久,自言自语道:“真像啊。”
像什么?他的父亲,还是他的祖父?
他很想问下去,她却摆手让他离开了。他终究没能问出口。
而当他再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全然是一介衰朽的老媪了。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他想。
直到后来,他自己坐上了那个位子,方才明白了祖母的孤独。
坐拥天下的感觉,其实是很寂寞的。
他仿佛再次回到了在东宫的那段日子。他无数次敲打紧闭的宫门,声嘶力竭地呼喊,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虎视眈眈的姑母,各怀异心的臣子……一切的一切,都让他精疲力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是织成一张束缚他的网罗,让他无处可逃。
他曲宴设席,延请众臣,以示恩泽。觥筹交错间,谈笑风生。他坐在南面的位置上,像个看客,旁观着戏台上的悲欢离合。
——这世俗的热闹与喧嚣,他听得最是真切,却皆与他无关。他倚在龙椅上,闭目听着新排的乐曲。
“不对,不对。”
他蹙眉,摆了摆手。
堂下的乐声戛然而止。
舞伎也停了下来。
“笙。”
他抬手指了一个方向。
内侍即下明白了他的意思。
今夜已是第三次出错了,他想。
为什么,连笙都吹不好呢?
枉费了他精心谱写的曲调。
本该可以尽善尽美的。
看来又要换一个新的乐师了啊。
“逐出,立杖杀之。”
乐师惊慌失措的求饶声很快散去,乐曲重新奏起,舞伎又缓缓起舞。
宴会在众人战战兢兢中继续进行着。
他侧耳听着他亲手谱写的曲调。
曼妙,真是曼妙极了。
4
花鸟使又为他寻来一双豆雁。
他日理万机,实在无心赏玩,便吩咐厨房烹了。
宫中是少有鸟雀的。先前女皇最喜鹦鹉,宫廷之中一时兴起养鹦鹉之风。也有人说那是女皇不喜猫的缘故使然。
近来贵妇间又喜养猫,宫里的鸟雀也少了很多。
终究是这宫墙太高了吧。
他又何尝不想出去呢?
“陛下,喜欢这红嘴蓝鹊?”
藩国进贡了一只红嘴蓝鹊,模样灵巧,在笼中上蹿下跳,与过往花鸟使为他搜罗的鸟雀都不一样,在一众贡品中尤为显眼,
他不知道自己对它算不算喜欢——只是,有种久违的亲切。
好像一下子回到了与母亲相守的那些日子。没有昏暗,没有空寂。雨时他依偎着母亲坐在廊下,看雨打花枝,听着雨点落在鸳鸯瓦上的声响;晴时母亲教他吹玉笛,弹琵琶,阿玉啁啾啼啭,庭中乔木扶疏。
那些记忆过于遥远,都有些模糊不清了。可当他一见到眼前的这只鹊,尘封的回忆一下子被唤起。
“尚可。”
他捧起鸟笼,像儿时一样从笼外细细端详着它。
与儿时的那只如此相似。
他忽然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
曾经无数个午夜,他从梦中惊醒,迷惘惆怅。他知道自己的的心里缺了一块,一个年少时就嵌进他心里的东西。
而今,他终于找到了。
金作屋,玉为笼。
他为它在宫中搭起水榭楼阁,在骊山上修建华清宫。
他夜夜枕着它的歌声入眠,每日拂晓为它用泉水梳理羽毛。
他在殿内起舞,一如多年前的那个夜晚。那本是他为母亲庆生准备的舞蹈,宫中对母亲之死讳莫如深,他只得在夜间为母亲祈福。而这次,他的身边多了阿玉。
那段时间,他好像又回到了孩提时期。母亲尚在,他仍是那个无人在意的临淄王。
不忧西风几时来,只怕流年暗中换。
5
潼关既破,他在一小支训练有素的骑军护送下逃出了延秋门。临行下,他手忙脚乱地将阿玉哄进玉笼中,藏在怀里带了出去。
他骑在马上,俯望着他的江山。这是他从未见过的风景。
儿时他的眼界,仅限于皇宫上方那四四方方的天空;弱冠之年,多是在宫闱中度过的;年岁渐长,他也仅仅流连于各个行宫之间。
宫闱之外的光景,他只有也只能在画师所呈的画卷上一饱眼福。但那歌颂的亦是他统治下的太平盛世,黎庶万民。城楼下的饿殍尸骸,郊外的萋萋芳草,就像是极不和谐的音律,此刻纷纷展现在他的乐章中。
他开始怀疑自己。
少年纵马逐猎的情景依稀历历在目,一转眼,就已经老了吗?
禁军行至马嵬坡下,溘然停下。
他抚着光洁的鹊羽,心下不解,却正听见众将以“妖异”之名,请愿他处死怀中红嘴蓝鹊。
为首的将领说得铿锵恳切,众兵士一呼百应。
他怔了一怔:“什么?”
“请陛下处死妖异,以安军心。”
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因震愤而发抖:“为什么?”
胸中郁结的愤懑在此刻爆发。他感到一股热血冲上头,随后是彻骨的寒凉。
“陛下玩物丧志……”
而后的话,他便听不大清了。
玩物丧志?
听来何其可笑。
可再可笑的理由,再荒谬的借口,只要积蓄得够深,就足以成为一把利刃,刺穿他的肺腑。
“陛下英名万世!”
他们满足了他最后一个微不足道的愿望,用白绫勒死了那只鸟,而不是用他们屠戮的刀。
他转过身去,看向灰青色的天空,似乎是要下雨了。
阿玉在他耳畔细声尖叫着,片刻就没了动静。
他余光瞥见了那个身材魁梧的将领轻而易举就拧断了阿玉的颈。阿玉还张着它的喙,鲜血从它的喉中缓缓流出,像极了啼血的杜宇。
他摇晃着走过去,一片片拾起地上的羽毛,敛在自己的袖中,然后径直向众人走去,骗身上马。
“走吧。”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后来他开始频繁地做同一个梦。
他常常梦见在东宫时的阿玉没有死,飞离了皇宫,在天空中颉颃盘旋,快活极了。
可是,很快,它落入了猎户的网中,又回到了他的笼中——可他亲手杀死了它。
它悲痛地啼叫,直到啼出血来,落在丹若花苞上。丹若花倏忽开放,映着月光,嫣红似血。
它死前凝视着他的眼神,时时出现在他的梦里,无助且幽怨。
“母亲!”
他从梦中惊醒,茫然地环顾着空荡荡的大殿。
他近来渐有些神志恍惚,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
他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成了太上皇,什么时候离开了多年的兴庆宫,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人,茕茕孑立地活着。
他究竟在哪儿呢?
他坐在殿前的石阶上,定定地望着宫墙上的琉璃瓦。
月光如泻,夜凉似水。
一切仿佛还是多年前的样子。
他又想起从前一直没有想明白的问题:那么高的宫墙,阿玉是怎么飞过的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只有他还是被困在了这里。
更鼓声终于响起。
一声声,一更更。
他起身,一步步走向紧闭的宫门。
此刻,星河耿耿,长夜将曙。
他垂垂老矣。
唯江山如故。

86

87

83

85

84

90

87

80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