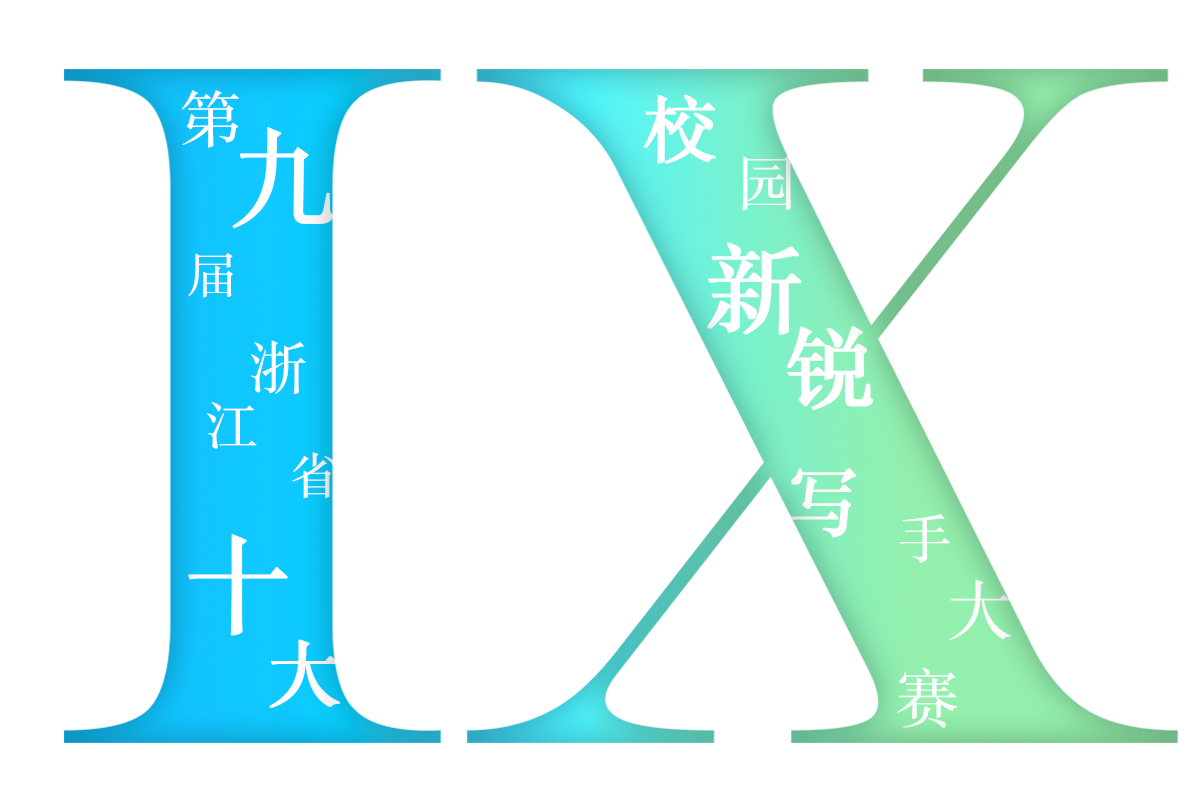叛徒
君非白 发表于 2022-08-30 17:34:46 阅读次数: 581556遇见白老汉那天,我收获了一株狗尾巴草,开着花,很好看。
烈阳下他穿一身白衣,颜色干净,与乡野间打赤膊的农夫格格不入——他们肚子上的肉皱成一条一条,沾着泥点,古铜色的脸上是粗犷率性的笑。属于乡野。
他递给我一碗水,粗瓷大碗,透着庄稼人味道。听我谈及与父亲的争吵,新闻学的理想,他不由笑了笑,那是一个当时我读不懂的笑,很放松,很晦涩……简直难以用语言描述。
他摸着院前的狗尾巴草,对我谈及尘封的过往。他那双手的动作是如此的轻柔,狗尾巴草的穗子没有抖落一粒。
我想我应该恨他,但不是为我漫长的童年。
这个月里我第三次拒绝入学。
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像食物碎屑旁的蚁群,在我心上爬过,又像狗尾巴草挠过脚底,痒痒的,怎么也抓不住。
祖母沉默着抽出我枕下翘角的书本,注视我。她松弛的眼皮已遮掩不住沉重的悲哀,尚存清明的眼珠祈求般转向我。
小时候那个男人教过我识字,他神色儒雅,身上的长衫一尘不染。后来他走了,只留下一堆泛黄的书,我,祖母。母亲在他身份曝光的时候含恨自杀了,投的湖,想来她那一身白皙的皮肉早被鱼群啃食殆尽了吧,渣都不剩。
她起身为我拾去身上的烂菜叶,叹息一声,嗓音像在砂纸上摩过,粗哑的不成样子,“你去吧。”
入学以后我逐步习惯了如此这般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对校园生活的困顿。我困顿于我的不知所措,师长复杂的眼神,解释身上不知名伤口的麻烦。困顿,演化成了长久的不适。
我是叛徒的儿子,我是要长成叛徒的。
你爸背叛了祖国,你不配上学。
你妈都死了你怎么不去死。
来后我的同学都是这样对我说的。叛徒,什么是叛徒?我不解了,只顾着对此深以为然,如此就好。
我只是不敢看祖母深沉的悲哀,我怕那双老态而清明的眼珠转向我,我怕她眼里成团的血丝。血丝,像流星尾巴一样的血丝。
教室里喧嚣一片,当然是与我无关的,我看着周围同学打打闹闹,说起隔壁学校的姑娘真是好看,可惜眼瞎喜欢谁谁谁。
我闭上眼,翻动书页,成了此间唯一的声音。
我只是时常拾起不轻不重地砸在脸上的纸团,茫然地抬起头,总是看见一群神采飞扬的男孩。
为首的那个看着我,轻笑道,“不好意思啊,我想扔向垃圾桶的,没看见你。”
我忘却了是怎样回答的,只记得当时垂下头,攥紧了手中满分的试卷。无意间瞥见门口的老师,他看我一眼,没有进门。
突然又是飞来横祸,有风掠过我的耳后,很舒服。打破平静的是一个易拉罐,尖锐的棱角擦过我眉梢,落下的是一缕头发。
没有受伤,我甚至想谢过这位仁兄。倒不是怕疼,每天一次的不小心摔伤难免引人担忧。
我依旧一言不发,他们骂了句没意思就转身离去,又聚集在一处说起邻校的那位姑娘。
我于是又困顿了,只记得他嘴唇一张一合,像一条搁浅的鱼。
你爹是个叛徒,所以你也是个小叛徒。
我从来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孩子。或者说,我从来不是什么值得被人喜欢的孩子。自童年起我就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我是在无止无休的烂菜叶、臭鸡蛋、指责里长大的,生而不堪,我的童年长得吓人,是一棵羸弱的狗尾巴草开出的花。
那时邻居家的小孩有一种别样的英雄主义。祖母却时常为我念起“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我拳头一紧而后委曲求全,是常有的事。
一日黄昏,我家菜园来了不速之客。半大的油鸡踩在瓜苗上,身旁趴着个被推倒的老人。周围有一群孩子在拍手叫好。
太阳溺死在云层里,最后一丝光被淹没了。
我的骨骼先是结成了一块一块的冰柱,继而快要碎裂了。我的身体里似有一座火山,沉眠湖底,待湖面出现裂纹,终将地动山摇。
我再也顾不得那位印度诗人所谓的“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我只看得见那倒在地上的身影。
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动作着,空荡脑海里唯有一个念头:看客的奚落与鄙夷是最悲的悲剧。
当反作用力使我的拳头遍布红痕时,我想我做到了。我终于能够扶起我的祖母。我笑了。
祖母没有笑,她那双眼睛里盛满了悲哀。她只是颤抖着手为我涂药,然后无言地炒了一盘菜。放了油。
第二天一早我看见她佝偻着身子挨家挨户道歉。提上了平日里舍不得吃的粮油。
也是。我是叛徒的儿子,再不安分守己,谁容得下我。
我企图清醒,企图沉默,企图把一切打倒在地。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我的每一拳都结结实实地砸在了自己的皮肉上。
很久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是白家的小英雄,书香门第,父亲是革命党人,母亲是战地记者。去小卖部买零食老板娘都会多塞几包。
不能再想了。
我掐断了狗尾巴草的茎,植物清润的汁液流了出来,滋润我干涸的皮肤,随之而去的是它旺盛的生命力。
他说到这,攥紧了手里那棵狗尾巴草。不出几秒就松了手,想来是意识到了什么。生茧的手掌顺着狗尾巴草的穗子轻轻摩挲。
太阳大了。他没抬头,汗珠子于是没有顺着下巴流下,避开了层峦的肉纹,滴在白衫子上。他盯着那株狗尾巴草,像望着被自己抛弃过的情人。
我也看着他,不合时宜地想起《人间失格》的开场。
“我这一生,尽是荒唐的过往。”
可他是如此冷静地讲述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事不关己,以至于冷漠至此。眼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只是回忆,只是讲述。把每一个画面刻在大脑皮层。
我试探着开口,“他……”
老汉终于抬头看我一眼,笑了笑。
后来他回来了。踏入门槛的第一刻我认出了他。
狭小方桌上摆着花,三个粗瓷大碗,盛粥,一旁是三个活物:祖母,我;他。
他照例是一身白衫,一尘不染,目光显露疲惫,澄澈到有些异样,先是把眼珠一动,转向如此眼神的出处:祖母已是一头白发,两鬓生华。脸上爬的是草根样的皱纹,纠缠不休。越缠越乱,越乱越缠,乱到不可收拾,缠到至死方休。澄澈之眼下耸两道小丘,其下捅出了两个窟窿,像土坑。脖颈也成了一道瘦骨嶙峋的月光。
“这是你儿子。”祖母嗓音带哑。
他又把目光投向我,粗布麻衣,满是布丁,倒是污了他的眼。他不关心我口味咸淡,不知我入了共青团,不管亲人死活组织命运,只顾做自己的选择。只一身白衣,干干净净。
果然,不久他又别开眼,看向祖母。祖母也看着他。没有人开口,只是长久地对视着,像两尊顽石,内里长出了青苔。
良久,他点点头,“对不起,谢谢。”
祖母也点点头,她说:“吃吧。”那声音像从喉咙底挤出来的。
他喝一口粥,筷子上结了薄薄的一层膜,一碰就破。后来他嘴角也结了一层膜。
“陈妍葬在哪?”他问。
“投的湖。”祖母答。
“把我也投了吧。”
他曾说死后要烂在土里,挺好的,湖底是一层土。
他没有葬礼,全部的陪葬是一坯黄土。
一如母亲。
此后我继续困顿,继续不适,继续抚摸狗尾巴草的穗子,等待它开花的那一天,即使除我之外的人永不会见到。它的花太小了,只有我能看见。
他死后我喉中仿佛卡了一块铁。有时我高仰脖颈,软骨处就要断裂,我于是不得不垂下头,眉眼服帖。小小的,一块铁,克扣我呼吸的频率,又不容置疑地增添了我生命的重量。为这不上不下的铁块,我忽而又轻松了。
“你叫白正,是吗?”
当时我正把玩着手里的狗尾巴草。闻言时愣了愣,应了一声。出声之人是新来的国文老师。
他眉宇间没有旁人的盛气凌人。他或许不知道,班级中家境再窘迫的同学,待我也是不屑一顾的。
“我观你行文有灵,待时事颇有见解,只是……你交上来的作业,我总觉着过于内敛。”
内敛。这个词用得还真是……我心中好笑,叛徒之子,怎么敢妄加评论。心中纵有十分激进,落笔时也不过三分。
他看着我,目光清澈,我反有种被那双眼睛看穿的错觉。“出身如何不是能选择的事,你只管写就是了。”
他起身准备离开,又是一句,“你在看马克思,是吧。”
我只觉晴天霹雳。
后来他时常与我针砭时弊,言语大胆,后来甚至唤了我一声同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敢的。
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过的一句话:伟大的品格是证明题,要用苦难来见证。
这位老师,真的和那人很像。但是那个人,是个伪君子。
我读马克思,本是好奇。后来也逐渐信奉这套理论,但是我想我没有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魄力,或者资格。
白老师不这么想,他说我行事慎重,才华出众,是个可造之材。他是第一个认可我的人。他目光里有天真,不是不谙世事的天真,有透彻,还有渴求。他像一个意象行走在诗里。
如果我能是龙傲天,他明目张胆地成为了玉佩里的随身老爷爷,明目张胆地关心,匡扶。邻座的人不再明目张胆地提起他,只是窃窃私语,声调高昂地窃窃私语。我不认为我已经不再困顿了。
拜他所赐,宣誓时责任已爬上了我的肩膀。
镜子里有个小白脸,衣冠整齐,镜子的裂纹搭在脸上,一双眼睛一尘不染,像他胸前的徽章,很透亮。和我是一个学校的。我觉得我嫉妒他,并且试图利用这张脸,从记忆里找出一个人名来。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白正。
这个名字年代久远,很早就被束之高阁。少有人挂在唇边。在那不可追溯的幼年,每一个认识的人都唤我的乳名,其他人都是一句白家的孩子。在我漫长的童年,我没有名字,唯一的称谓是一声“喂”,我常常疑惑被叫到的是否是我。能被准确识别的是狗东西之类。毕业了,几乎人人都唤我同志。
我唯一使用这个名字之地在于名册上。年少时我时常疑惑这是否是我的名字。
这个名字曾经是我被提及的理由。很久以前他唤过,再然后白老师唤过。毕业三年了我依旧唤他老师,他是情报组的副组长。而今我又有了被提及的理由,我有了一个代号,很可惜不能告诉你。我不再困惑,并且可以去死,为了不可宣之于口的光荣的事业,我的名字也是我去死的理由,但是我尽我所能地活着。
我不再嫉妒镜子里的人了。
狗尾巴草上失掉了掐痕。我的童年结束了。
我时常向他问起那位神秘的组长,他总是深深地看我一眼,不做言语。很久以后我才得知,那位组长过世已久,只是留了个名头,已全悼念之意。
我说:“是个很美的故事。”很深邃,很救赎,像狗尾巴草劲瘦的腰身一样。
这位白同志看我一眼,“是吗?”有一瞬间他目光里困顿在厮杀,然后坚定取而代之。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位不可提及的组长是我的父亲。或许是想到了的。
四十年已过,我等来了一纸薄薄的公文。
白清允同志深入敌内,搜集大量可靠情报,并多次掩护同志转移,为党的事业英勇献身。
陈妍同志为保护重要文件并掩护其不幸牺牲。
特追封为烈士,为之正名。
这里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连以来却怎么也不明白。
他们都入不了烈士陵园,那方死寂的水潭是我们一家的归宿。
我想宽慰他,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这么多年的怨,就是个笑话。
他看着我笑了笑,轻松又自在,手里还是那株狗尾巴草,“我妈走了,他走了。祖母走了,白老师走了,我估摸着也要走了。这往后的事啊,就看你们年轻人了。”
访谈的最后我对他说,“好。”
显然,完整版的故事更为深沉,也更刻薄。
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看待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好几次想要张口,在他看来该是一言不发。
我想写一些,英雄背后的故事。
白清允前辈是我们,是人民的英雄。是铸就我们可爱的祖国的先辈中闪闪发光的一个。之于白老汉,不,白正同志,还有他的祖母,是彻彻底底的叛徒。他们有足够的立场去指责。
可他同样是他们的英雄,至少他的孩子可以上学,至少他的后辈守护了他的孩子。至少他让像他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总要有人挺身而出的。
不久的将来我会是一名战地记者,我知道的。回头一看,狗尾巴草的花分外好看。
(就当背景架空吧,求求了各位老师不要考究)

90

91

80

89

86

86

80

86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