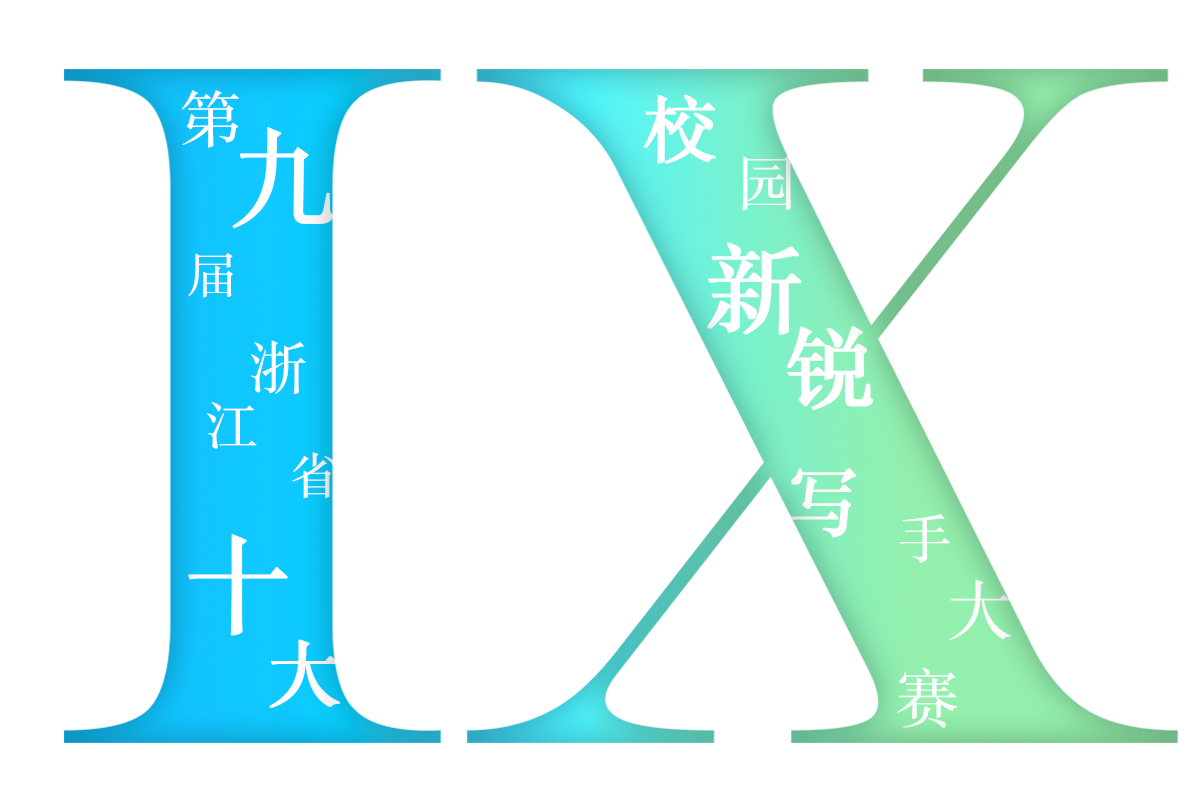归家须尽欢,穗穗平安
倪文仪 发表于 2024-05-19 19:40:32 阅读次数: 2283一枕黄粱,我寻光之脚步,追流水之所向。
梦醒,南柯黄粱终成空,但少年心性,终是停不下脚步。
江南,最是人间好风景;江南雨,最是人间留不住。
江南的杭州,微风一吹,身旁松柏绿沉的叶发出阵阵声响,就像一根定心针,驱散了阴霾,使人放松。来到西湖,水平如镜的湖面令人不忍心打破,走过的路人仿佛都放慢了脚步。远远望去,船上似乎站了对有情人,手指远方,憧憬着未来的点点滴滴。雷峰塔屹立,静静地立在河边,见证着岁月流转,影光蹁跹。层层树木翠绿,雷峰塔“直冲云霄”:白日与云朵比肩并起,夜晚与明月比肩而立。
倒映在水中的花,你是否也在寻找那个他?和风一吹,“镜”中的一花一木一塔皆支离又破碎,不下一会儿又恢复平静,周而复始。如一场评戏,说书人笑着:“今儿个,咱要讲的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是如此地遗憾啊,一场好戏失了结尾,如同人失了初心,怕是在这吃人的社会,屈辱地留下了辫子,满心欢喜地穿上三寸金莲。被恶臭的言语吞没,终是走进了那张嘴:封建礼教。你困住了多少生命?
摇曳的炽热日光,悠悠地从“很久以前”讲到“很久以后”,千年的时光,仍道不尽他的梦想。走断桥,赏荷花;看世人皆赞叹的三潭印月;品独特风味的龙井茶,虽苦却又醇香,道尽了人世间苟且与美好。你在透过这青绿的茶汤,看谁的影子?
他还会来吗?被困在历史的长河中,那是他无法割舍,也无法逃避的。王者之剑,你曾照应着谁的荣光?
阳光从倾斜的草坪上滚下来,“小心,可别弄伤了他!”那关切的声音不假,他们不管眼前的黑暗,带着光明奔来。回头看,冒着黑气的沼泽,黑洞洞的漩涡,无不将他们吞没。“砰——”雪崩了,人们的信仰在此刻崩塌,这是一场人性的表演。
“真是,假爱国,其实都是卖国贼吧!”“资本家!”“有什么用呢?”
是啊,有什么用呢?你们希望月光能照破万朵黑暗,将光明带去万家,便下定决心不再看月亮。可月光穿不透你的眼,照不明你的心,还能找到曾经的影子吗?红色的雨下在我眼前,如血般灿烂,洋洋洒洒。如他一般,刚展尽锋芒,春风得意。便被这世界规则匆忙请下台去,因为“好戏要开场了”。
从活泼的夜莺变成哑巴需要什么?只需要一张嘴,一场舆论。百万的数字庞大,可看着流落在外的他,终究还是不忍心吧。我的孩子,何时才能归家?“拼拼凑凑总会有的。”你们在笑,笑的仰天又伏地,只是眼泪不合时宜地出现在笑脸上,泪水黏黏糊糊地扒在脸上,总是显得凌乱。
叮咚!下一站——瑰葭路。
他回来了!1342公里,是他归家的路。你们是否记住了他的名字“越王者旨於睗剑”?
夏日的雨总是沁凉的,绵延的珠子断了线,大把大把地撒向湖面。湖中或许如深渊一般,凝视着你。一颗颗珍珠被尽数吞没,只留下一圈圈涟漪……好好看看江南吧,那是他的念想,你们的故乡,我的家乡。
一再遇,莫别离
我再次见到了他。他一身登山装利落,身后背了一把小黑金。他就如此站着,态望向那东北角。飘动的发丝遮住了他脸上的神情。那眼神似是奕奕蹁跹,似是黯淡天光。我看不清,他站在阳光下。
我向前走去:“吴先生……”话还没来得及说完,我便后退了一步。他的神情像那长白山化不开的雪。周身的低气压化为实质,阵阵寒气将我定格。
我曾听说过他,吴家的小三爷…小佛爷?清新脱俗小郎君,
出水芙蓉弱官人;如今再见,也难怪如此评他。
“小天真——”他的身旁突然凑来了一位胖子,同样的穿着,却略显庸肿,头发微卷齐肩,活像一位搞艺术的造汗。胖子搂着他的肩膀,亲昵地叫着。“唉—胖子,你可瘦了!”他忽然笑了。仿佛是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鄙夷着,眼前这位小郎君实在不像那说谎的主儿。可对那句“瘦了”我是万般不会信的。只得当他是朋友间的客套寒喧罢了。
那胖子的手实是不老实,说着,手伸进了小三爷的口袋,让我形容实是大胆得偷偷。那小三爷似是不觉,袋中的烟轻而易举地便被夺了去:“小大,你不得道,这好东西肯定是要胖爷来享受的!他从中抽出一根可借个火”“死胖子”虽是如此座答,但仍是:双手伸向前去。香烟燃了,顿时,那烟喷了出来,白色的烟如纱掉我与他们分隔。走不出,看不破。忽的,一阵笑声吹散了这层屏障。“死胖子,套路我——”小郎君脸上梁上笑意,眼角若隐若现的鱼尾纹再也藏不住他心底的蜜色了。
都收拾好了?”远处传来一声,语调上扬。好似那王熙凤,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我伸脖子望去,那人一双丹凤眼,眼眉间皆是盛气般地上挑,极向那名角花旦,似是天生无需粉墨描绘,往台上一站便是满堂彩。他似是注意到了我,冲我颔首,说道:“解雨臣”可身边的人都叫他花爷,不解,却也是如乡随俗,同他们一般如此称他了。
他只是站在一旁,玩着手里的俄罗斯方块,一身粉衣,在这个灰色的场景里,是唯一的生气。“小花”小郎君喊道。那两个字里似是浓墨,皆是化不开的情感。花爷没应,手机中游戏失败的声音迫使他放下手机,抬眼朝着说话之人望去。“哼,又准备一个人去冒险。”他明明说得轻淡写,却让小郎君慌了神,欲解释,可到了嘴边的话都又吞回了肚子,一响沉默。
再回过神来,花爷身后早已站了一个人。那人搭着他的肩膀,用手拍着他的背,似是在帮他顺气。嘴中悄悄说着什么话,真叫人把气儿,了,紧皱的眉头又松。“真是奈不住你!”说着,一把把那“保锶的手挥开,走向前去,拎住了那小郎君的衣领“别让我们…”话只说了一半儿,便离去了。
“哎。我说天徒弟,这么重要的事儿不通知我们!让我们家花爷儿日生气”说话那人带着一副墨镜,穿着一身沉闷的黑色,怎么看怎么像保镖。按摩“这位小姐,要不要办张卡,盲人服务。”
我伸手接过了他递过来的卡片。“黑眼镜——”我念出了明片上的名字,”真是个奇怪的名字。“嘿嘿,不过天多数人都叫我黑瞎于!”是个黑店吧,我心中想着。那小郎君居然交了这么多狐朋狗友。
二离别,须尽欢
他们向那远方去,我心下明了,那是长白山的方向。故人远去,何须叹!离别之时终释怀。他就这样,大胆地往前走去,不再回头。长白山的另一头是何方?我知道,那是终极,是无数人掩盖的秘密。
睡梦中,我看到了长白山的雪,还是冰冷的化不开。周遭没有声音,仿佛从未有人来过。可我却看到了一行人的脚印。是他们,他们来赴约了。十年之久,七年之痒。
青铜门启,那人走了出来,“你老了”他说道。
“嗯,接你回家”小郎君答非所问着。
他朝若是同淋雪,也算共白头。只是沙海事变不复当年模样,血丝布满双眼,那是谎言。疤痕蔓延手臂,那是风霜。心脏剧烈跳动,那是终极,是十年接他归家的路。
我又想到了那把剑,曾经也是这位小郎君让它重新回家,几千年,思念化成风早散在了布满尘埃的空气里。刀身锋利,如同那人眉目健朗,照应着过去和未来,却唯独看不清自己,多情亦是薄义?
从长白山顶一路到山脚,路途无疑是漫长的,可小郎君并不觉得。他曾走过无数次,无不是伤痕累累的,只是这次故人归。他又是那桀骜少年郎,不信苍天不信鬼神。
到最后,他清醒着,庆幸着,夕阳仍照在他身上。
后记
他们回到了雨村,只有胖子,小郎君和那位不爱说话的人。从长白山回杭州的途中,他们特意与我来道别,我倒是受宠若惊。“很高兴认识你,小姐”小郎君说到。他到底是做了个说书人,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皆安”我说道。
“妹子,一路顺风啊!”胖子说道,他从来皆是如此,不拘小节,却是那重义气的。不知云彩姑娘是否还记挂着他呢?但愿不了吧,云彩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她来这人间一趟,为一个胖子带来了云彩朝霞,影照浮世风流。愿他们都能如愿,也愿他们都能放下。
“小哥——今天吃什么好吃的?”
“小鸡炖蘑菇。”
“小天真你站住,我养的花怎么都蔫了?”
愿他们皆安,归家须尽欢,年年岁岁,穗穗平安。

 |

 |

 |
范德清 |
张利利 |
汪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