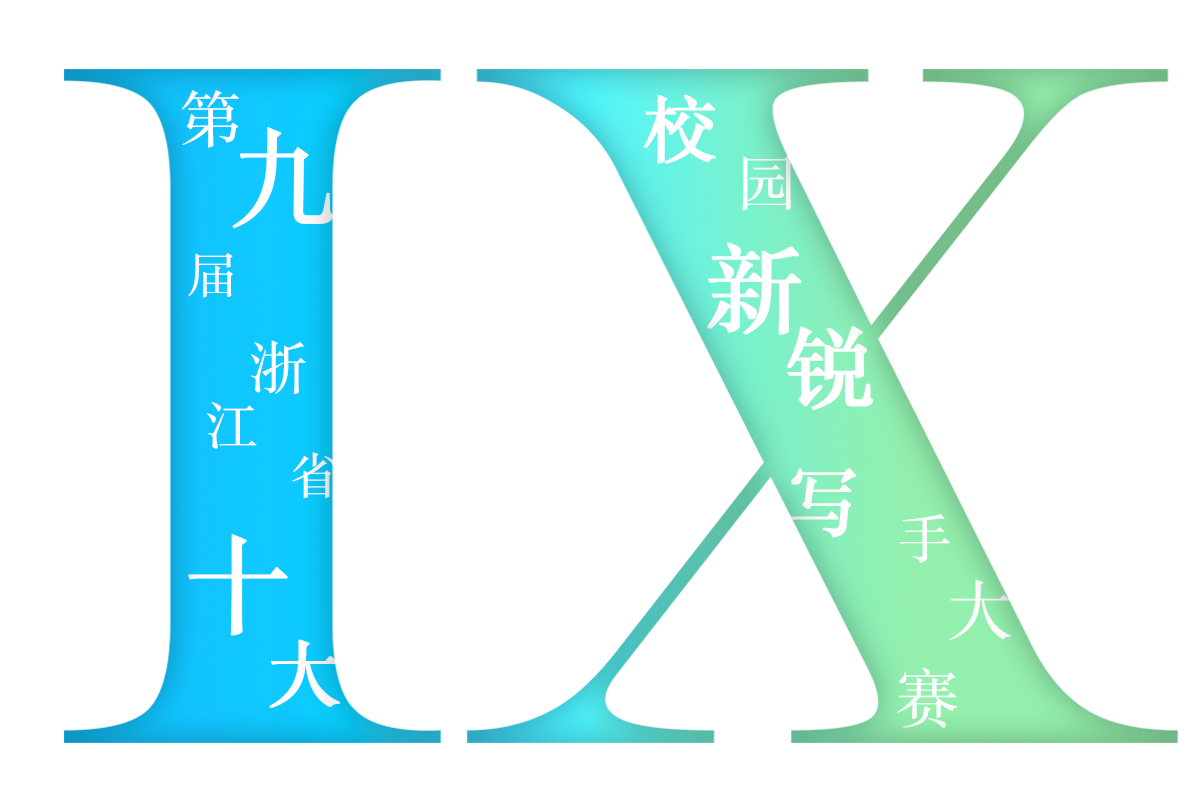天一定会亮的
小血落枫叶 发表于 2024-05-11 20:43:56 阅读次数: 754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出现过的欢乐和痛苦都呈现同样的底色,在泛黄的纸上黯淡无光,难以区分。命运几次三番扼住我的喉咙,把我变成夏天闷热湖面上的一条将死小鱼。每当这时,脑海中不停浮现出一个巨石般的背影,他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太阳,满身光明,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他动摇一分。这使我相信,天一定会亮的!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母亲在鬼门关做了笔交易,拿自己的性命换我来到这世上。奈何连鬼神都要作弄她,以命换命的孩子偏偏是一个可笑的残疾。我的嘴永远斜撇着,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支支吾吾令人难以理解,就这样一个残缺的我夺走了母亲的生命。
我出生的那天的事,亲戚们讲过很多,都记不太清了。难以揣测那时父亲的心理,或许吧,他也喟叹命运的捉弄,他也想抛下这一摊子烂事一走了之。面对这一切,他没有逃避逃避,他之所以能成为我敬重一辈子的人,就在于他对命运的忍受,亦是另一种抗争。
在我看来他是最有资格抱怨的人。七岁那年的高烧带走了他说话的能力,落下残疾,此后他就只能和自己的内心交谈,和灵魂对话。父亲同万千劳苦大众一样,瘦小,黝黑,山大的责任使他单薄的背总是弯曲着。他历经万难,活着,命运的绳索始终套在他的头上,当生活有点起色,这该死的绳索就收紧一分,无数次妄想勒死父亲。
面对这些,他就只是坐在那儿,坐在医院外的黑暗里,静静地等。如今想来,他总是这样,在生命长河里,宛如一块巨石,任凭激流砂石如何冲刷都巍然不动,永远静默,坚忍。大地一样粗糙的双手在脸上不断“莎莎”地摩挲着,就这样默默等着。那天的夜很长,很黑,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在等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黑夜终于散去,东方泛起鱼肚白,天亮了。
几天后的一个玫瑰色清晨,父亲毅然决然地带着先天残疾的我坐上回村的面包车。一路颠簸摇晃,他打开窗,让一丝微风吹抚到我的脸上。我睡在父亲的臂弯里,像是在温暖舒适的婴儿床里。
父亲是一名手艺精湛的修鞋匠。街坊邻居都是好人,心善。他们或是怜悯我父亲,或是钦佩他的勤劳坚韧,客人总是络绎不绝,叮叮当当的修鞋声编织成曲,萦绕了我整个童年。修鞋费街坊们总是愿意多给,可父亲坚决不收,从来不收。他只拿自己的那一份,对于别人的善意,他总是飞快摆手,将多的钱塞回他们的口袋,笑着送他们走出店门。面对善良的街坊,父亲用行动教导年幼的我,善意是相互的。父亲在给他们修鞋的时候总是愿意多上胶,多上布料,修得格外仔细,保证一年半载不会再坏。可这样的保质保量的修鞋,街坊们的鞋也总是会“莫名其妙”地坏掉......
街坊们是好人,可他们的孩子不是。年幼的生活总是被孤独地灰色笼罩。跳房子打弹珠这类的游戏他们从来不许我玩,他们说等我什么时候学会好好说话才能和他们一起玩。我不服,总是蹲下来,呜呜叫着做出几个可笑的鬼脸,然后转头就跑,被一些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撵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恶毒一些的,骑在我的身上,一只手抓着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摁到土里,盛气凌人,恶狠狠地说:
“快说,你是不是傻子,连话都说不清的傻子!是的话就点头承认啊!快点!”
被摁倒的我吃了满口的土,身上的重量使我难以呼吸,周围的孩子疯狂拍手叫好,他们中间充斥着快活的空气。我在痛苦和屈辱之中点头,他们似乎没有看见,或是故意的,就不松手。我只好更拼命地点头,眼泪包裹着屈辱一起落到泥土里。
我满脸灰尘泥土地回到家,父亲在研究修鞋的胶水。看到我这样,他好像明白了我遭受的事,默默地给我洗脸,洗澡。一个人走到门口的台阶上,坐下,长久出神地望着远方的天。天慢慢暗下来,黑暗如潮水般将父亲吞没,我感到他的痛苦是我的几何倍。矮小瘦弱的他却像是一块饱经捶打的巨石,静默且坚忍。门外的夜无比漫长,我不知道天什么时候亮起,可是看到父亲坐在门口的背影,我更加相信,天总会亮的。
后来的我依旧朝他们做鬼脸,又是无数次的屈辱。当我的脸因为埋在泥土里而眼前一片漆黑难以呼吸的时候,脑海中总会闪过父亲静默坚忍的背影,于是乎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像块巨石一样,任凭他们怎么霸凌都不肯点头,再也不认自己是傻子。
跑啊!我拼命地跑,我跑得飞快,快到再也没有人能追上我,再也没有人能够把我的头摁到泥土里。回头望望远处气喘吁吁的坏孩子们,我兴奋地蹦跳着高声疾呼起来。我知道我跑赢了他们,跑赢的也不仅仅是他们。我感到此刻黑夜散去,属于我的晨曦到来,天亮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就算我跑的再快,也没有人能让我抗争了。我看到他们背上五彩缤纷的书包,迈着轻快矫健的步伐走向学校,心里像是有一万只毛虫爬过。
街坊们也常常和我父亲讲,老张啊,孩子到了年龄就要上学,大人苦点累点孩子也总要上学啊。父亲看见了我眼巴巴望着别的孩子的可怜模样,低头更加卖力地修鞋。他无声地笑着点点头,给这个客人多上了一遍胶水。
我想上学的念头愈发急切,我躲在教室窗户底下,偷听他们上课。我迫切想和同龄人一样,坐在干净明亮的教室里读课文,学知识。终于,在一个夜晚我忐忑地告诉父亲,我想上学。父亲点点头,用手指告诉我了两个字——等着。
父亲又走到门口的台阶上,坐下,凝望着远方的逐渐陷入黑暗的天空,等待着。父亲叫我等着,我便等着。我知道,只要和父亲一样等着,等着,天一定会慢慢亮起。
父亲熬夜修鞋,乒乒乓乓的修鞋声响彻半夜,为了多赚钱他将好久不拿出来的配钥匙开锁修锁等一系列高难度的手艺和设备都拿了出来。通过父亲超人般的努力,我成为了旁听生。
上学的日子快乐又充实,是灰暗童年里一抹亮眼的色彩。通过课文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个伟大的灵魂叫史铁生,和我们一样也是残疾人,如今,他已经在满是朝阳的山坡上奔跑了。还有一个人叫保尔柯察金,他是一块真正的钢铁,他找到了那片永远为他而亮起的天空。看到他们,我时常想起还在一刻不停修鞋的父亲。
当我看到人类伟大的灵魂时总会流泪,这无关乎国籍,无关乎岁月。所有的灵魂总是会遭受无尽的黑暗,这黑暗里藏匿着荆棘毒蛇,漫长的黑夜,痛苦的煎熬。人的伟大在此刻显现,忍受一切,穿越一切,内心的那片天空一直亮着,未曾熄灭。
每当我流泪时,同学们又该笑话我了,他们说,那傻子又哭了。我不在乎,他们没有经历过天黑,当然不知拂晓时分的快乐。我心里对父亲满是感激,他是一块真正的巨石,一块顽强的巨石,永远屹立在我心中。
父亲用那微薄的收入支撑着我一切消费,整整九年,虽然中考失利,但我已然十分满足,没有任何怨言。是时候回到父亲身边,专心和他学手艺,帮他分担生活的压力了。
父亲精湛的手艺很难学会,他的双手灵活巧妙,像是两只上下翻飞的雨燕,在来回不停地穿梭中将一双双旧鞋变得崭新。
修鞋,看着简单做起来很难,满手是胶不说还时常被各种锥子刀子伤到手,血流如注。我常常怪自己,为什么这么笨,练习很多次的东西到了真要用上时总是使不出来,急得泪水吧嗒吧嗒地滴落。在泪光朦胧中看到坐在我对面,耐心教导我的父亲,他黝黑的脸上永远挂着宽容慈祥的笑,脸上的皱纹也随之挤到一起。他那如同古希腊雕塑般有力健硕的双手除却老茧外全是伤疤,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疤,看着像是孩童奇怪的涂鸦。他也被锥子、修鞋刀划伤过千万次,让我想起上学的时候看到过的一句话,美玉只有被刀雕刻上万次才能成为艺术品。
咬咬牙,坚持下去。学习手艺是很苦的,就像是走在一条从未走过的黑暗小路上,不知道下一脚踩下去是结实的大地还是无尽的深渊,不知道路的尽头在哪儿。我只是知道,只有坚持,忍受,默默等着,天一定会亮的!
常言道,过日子就是白驹过隙,学习手艺九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我承担起修鞋铺的主要职责,父亲也只在我遇到棘手的问题时给予技术指导。我将修鞋铺关门的时间延长,买来新款的鞋子在店铺内出售。我更加忙了,也更刻苦,店面的生意日渐红火,父亲的脸上笑容也越来越多。我从未告诉父亲,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秘密。我想要攒钱,买一所不大不小的新房子,和他两个人住在里面,给这个一直领着我等待天亮的领路人养老送终。每当我想起父亲开心的笑脸,就算是正在给别人修鞋,我也会不自觉傻笑起来,客人也一起笑。这些其乐融融的时刻,都让我感到黑夜正在褪去,天就要亮了。
小时候的我以为抓住了蝉就抓住了夏天,后来的我以为有了钱就能带父亲过上好日子。可一切好似是诅咒,当生活都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命运的绳索就不知不觉开始收紧,索要我的性命。
在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父亲在店内喝粥,突然捂着胸口,眉头紧锁,一脸痛苦地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救护车呼啸着将父亲和我拉到医院,看着抢救室的红灯亮起,我感到有东西勒住我的脖颈,难以呼吸。
再次见到父亲时,他躺在病床上,眉头微微紧锁,黝黑的脸却透露出苍白,脸色非常不好看,面部显得更加瘦削。医生面色凝重地拉我出来,他和我说,你父亲是恶性肝肿瘤,通俗点讲就是肝癌,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肝功能丧失大半,已经回天乏术,都到这步田地了还不倒下,这老爷子也真是能抗。我没有思考,问医生如果要治疗,该怎么办。医生不假思索地摆摆手,告诉我这是一个无底洞,人财两空,完全没必要,保守治疗能给老人最后的体面。
说完就领着一群护士走了,回忆医生刚才说的话,这莫大的灾难令我陷入无尽的黑暗之中,如同年幼时分被摁入泥土之中,难以呼吸,我感到天空似乎再也不会亮起了。
这时父亲已经完全清醒,亲戚们都来了,他们望着父亲,全失了声。表哥拉我出去,对我说,你爹的病我们都知道了,你不是还要买房么,掏空家底也不够治的,根本不值当,放弃吧。大舅在我身后拍了拍我的肩,摇了摇头,同样示意我放弃。我低下头,一句话没说,只是回到病房内,拿起棉签给父亲嘴唇上涂了点水。抬头,对上父亲的双眼,他的眼睛平静如水。在他这一辈子里,他的眼睛一直如此,善良,痛苦,静默坚忍,认命却又永远在和命运抗争,如同一块巨石般平静地忍受一切。就在此刻,他终于要向命运低头了。他微笑着摇摇头,将我的手掌拉过去,在上面写下俩字——等着。这次,他同往常一样叫我等着,等他死,等他陷入黑暗,等他永远将自己的天空熄灭。
环顾四周的亲戚,大家都劝我放弃,这一切的一切到最后都是徒劳无功,连我父亲自己似乎也已向命运低头认输。回首我的前半辈子,命运一直扼住我与父亲的喉咙,可不管命运怎么蹂躏我们,我们都一起忍受,一起等待天亮。
生而不养枉为人,病而不救悔半生。当初父亲并没有抛弃我这个残废,如今我也不能抛弃他!没错,我大半辈子都在等,可这次,不等了!我要自己去找那片纯净明亮的天空!
既然他们都说我是傻子,那就让我再傻一回!
想到这里,我抬起手,猛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搪瓷杯随之猛地蹦跳了一下,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长久的沉默,我用自己毕生最自豪的声音吼出了一个字:
“治!”
八月四日凌晨四点,距离确证肝癌过去了半年时间,父亲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我知道,最后的日子就是今天。狭小的病房里挤满了亲戚,每个人的眼中都饱含眼泪,他们都来送这个善良而伟大的男人最后一程。父亲已没有力气再用手比划任何事了。我望向他的眼睛,感到他眼里的平静湖水起了滔天骇浪,猛烈冲击,似要冲破枷锁。我明白了,这个和命运斗争了一辈子的男人其实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仍然没有放弃,心底依旧想再抗争一次!
“走,爹,回家!”
我磕磕巴巴地将这句话说完,在所有人震惊的注视下,卸下保险杠,将骨瘦如柴的父亲抱起。我看到他眼角闪出泪光,四十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哭泣,也是最后一次。
正如我出生那天的父亲一样,我毅然决然带着风烛残年的他坐上了回家的车。一路上,面包车颠簸摇晃,我将他的头贴在我的胸口,父亲在我的臂弯里熟睡,像是睡在婴儿床里的一个安详快乐的婴儿。这半年,花光了我毕生积蓄,整整五十万!我从未犹豫,从来没有停下尝试点亮父亲天空的脚步。想到这里不禁笑出了声,果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真是凑巧啊,老天怎么知道我刚好有五十万!或许我是真傻吧,我并不后悔,甚至万分庆幸我的积蓄刚好能够用来挽救父亲。
我知道,在这次和命运的较量中,我输了。
或许吧,我是一个真失败者,可我此刻却挂上了胜利者的微笑。
我推开窗,让微风能够吹抚到父亲的脸上,极目远眺,透过墨绿色的崇山峻岭,在雾气缭绕的玫瑰色清晨里,一轮红日正缓慢地爬上山头,漫长的黑夜过去了。
快看啊,父亲,天亮了!
谨以此文献给我同样静默坚忍的父亲

 |

 |

 |
范德清 |
张利利 |
汪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