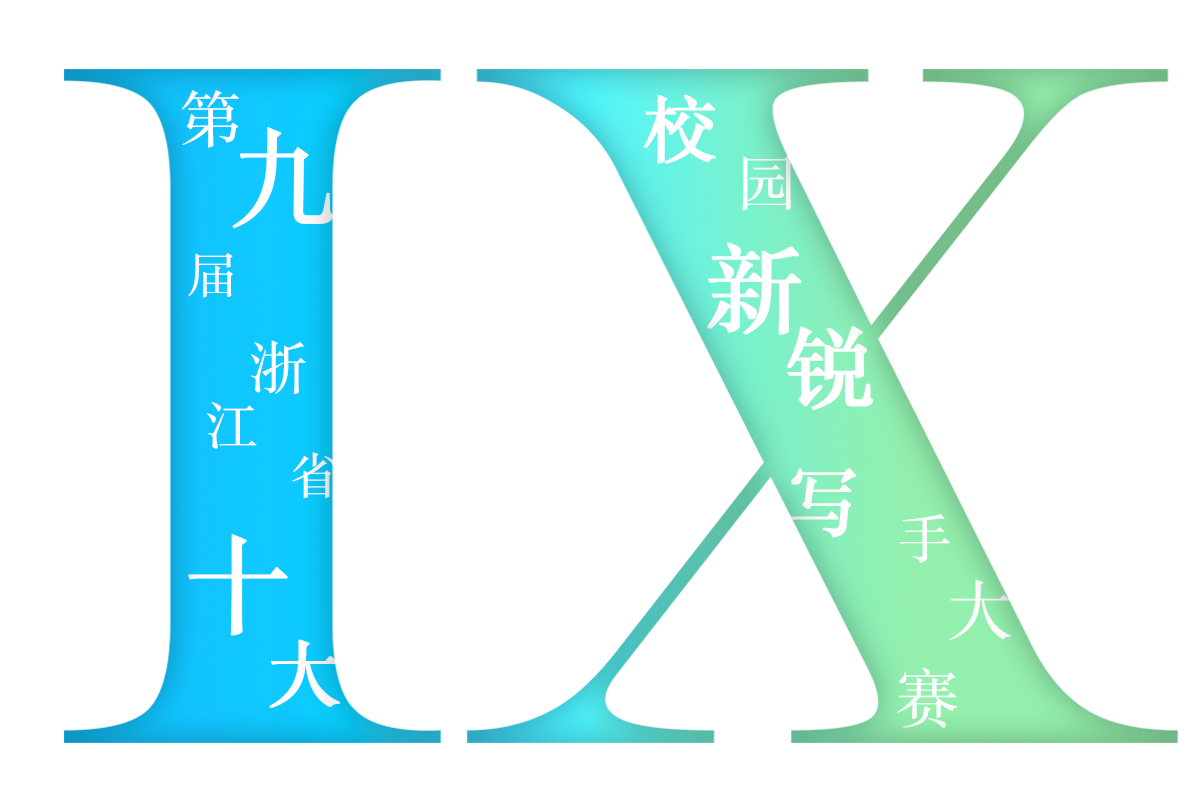外乡人
疼也现身 发表于 2024-05-02 12:41:16 阅读次数: 70李二从小就没有妈妈,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这件事很容易理解,不是所有的人都过着四平八稳的日子,有些人刚出生就面临了一道又一道的坎,好像有谁在阻碍他们向幸福靠近。李二作为一个寒门学子,很早就理解到了这个道理,大概是他进小学那一年,所以成年后也接受了这一部分的残缺。本质上来说,他和他爸还是能组成一个足够圆满的家庭,就像一个跛子也能自如走路,一个瞎子看到的世界没什么不同,只是遇上写作文要做些虚构,有时也可以大方把这件事列在纸上,这是极少数。等他十九岁念大学的第二年,他爸也莫名离世了,这就代表着他彻底成了一个跛人,不是光靠装样子就能正常行走的,幸好他已经接触了广阔的社会,也计划好了接下来的五六年该怎样过。它们本来是出于闲暇中偶然的畅想,现在成为了一个合理的支柱,好像从萎靡的两脚间又生了一只脚,勉强可以继续走下去。得知他爸走的那个晚上,李二收拾好寝室,扔掉了桌上的零食袋和瓶瓶罐罐,系成一个大垃圾袋,他也把衣服洗好晾着,嘱托室友过两天把它们收了,这样他那一角就不会在之后几天散发出闷臭味,他有时会闻到它们,可其他人闭口不说。三个室友都是很好的人,他不想让他们难堪。做完这些,第二天早晨他背上背包离开了学校。
回乡的路途十分平淡,手机玩一上午就没了电,李二几次欲入睡,总又被大巴的颠簸晃醒。在梦里他粗略地回顾了自己与父亲的一些纪念时刻,有一次他语数都考了满分,回家里给他爸看。他爸打量了一遍,说,好啊,真好啊,你要保持这样的好成绩,以后考出山去,别再当山里人了。转手给了他十元零钱,这十块钱他揣进笔袋里,后来买了好多五毛的小零食和小玩具,那些小东西的样子记不住了,倒是那张十块钱记得清晰。还有一次他被学校的几个小孩揍了,每一下都打在他硬实的肌肉上,痛感很结实,这一架打下来算是难分秋色,两拨人互相嘲讽完就分开了,他几乎是一步一跪爬回家里。回家躺在床上,李二把事情一五一十讲了出来,呻吟着问他爸,你能不能明天去学校帮我打回来?他爸摇了摇头,成年人怎么能和小孩动手。李二爬了起来,说,那你教我打拳,我学了去把他们打回来。他爸好像吓了一跳,说,你怎么知道我会打拳。他说,你经常早上起来不在床上,站院子里动来动去,拿根棍跟挥剑一样。你以为我是瞎子?他爸看了看他说,你要是打不过的话,就揣根棍子去吧,照着腿打,别打头。他说,他们也会拿棍子。他爸说,那你就拿根更结实的。李二说,你为什么不教我打拳?他爸说,别问。然后他们不再说话,像是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得精疲力尽,靠在一起睡着了。
李二其实有个哥哥,上小学二年级他爸才告诉他,起因是他追问自己的名字有什么意义。他爸被问得烦了,只好说实话:他哥生下来的时候,夫妻俩捧着字典找字,希望给命里添个彩头。李光,李富,李享,最后商定了立这个字,不求财运,不求仕途,不求人生美满,只希望他顶天立地,是一个正直的男子汉。李立三岁那年发高烧死了,几乎是一晚上的事,他们还来不及寻医治的大夫,就在热毛巾下静悄悄地死了。又过两年才产的李二,谁知这回换他妈走了。李明贵抱着李二走在回家的路上,十几分钟的路变得如此之艰难,四周漆黑,心痛如绞,他什么字也想不出来,或者说已经没有心力再去想,一回忆起当初翻字典查找几天几夜的情景,仿佛又要生出几根白头发。李二说,那我的名字怎么办?他爸说,等你以后有工夫了,自己去改个好听的吧,叫什么都行。现在他忽然想到了这句话,觉得这个时刻差不多到来了,以前他不太在乎,但现在应当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可叫什么好呢?他从来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即使他已经规划好了未来去哪座城市读研,选择哪个专业深耕,他也预想好了那些第一次知道他名字的人诧异地来询问他,然后他淡然地解释缘由。这个问题好像一直攥在他爸手里,现在苦涩地交还给了他,可是他竟然从来没有想过。
下午大巴在村外的镇子停了下来。村子在山的高处,镇子落在山腰,李二小时候常来玩,这几年已不怎么热闹,大部分店铺已倒闭,来往行走的人也都垂垂老矣。李二吃了碗面条,然后找了一个车上午睡的摩托车手,付给对方十二块钱,上车即走。上山时他琢磨着,以后多久回来一趟算好,给爸又烧点什么,他都没啥头绪,他爸还没有教到这。也应该说对于这个事情,他和他爸都还没有做好准备,他爸今年四十六岁,身子算硬朗,再加上时不时要打拳,这些印象盖过了现实的关心,让李二对他爸健康的了解蒙着一层面纱。那通电话也没说他爸死于何故,电话是他大伯打来的,只是向他宣布了死讯,让他尽快赶回来,他的脑袋在一瞬间空掉了,什么疑问都提不了,下意识说,好的,谢谢了。上山的途中,疑问越来越多,像云朵一样跟随着,一路斡旋到了村口。大伯在屋前接待,屋子上了锁,大伯说,里头没多少东西,都给你整理好了,待会你进去看看,有什么要带走的。李二道了声谢,接过钥匙,扭身走向屋门,打开门后,一股刺鼻的臭味窜出来。他花了一下午把整个屋子掏空,屋子里没有一丁点阳光照着,好像它也已经死了。没用的东西都腾到了空地上,一张木桌,角落里的酒瓶,木柜里的照片,日记本,里头没有文字,以及一个坏掉的照相机,并没有装储存卡。奇怪的是有一个包裹,打开来是一些古董样的金属,李二想了一会儿,回忆起这是高中历史书上的刀币,一种战国时的货币。他历史学得不错。父亲还有收藏古董的爱好?
收拾完垃圾,李二把日记本和包裹装进背包,当晚坐进他爸的灵堂,披戴上白衣白帽,准备守夜。堂里七八个亲戚围着两张桌子喝酒,打麻将,还有几个小孩在地上乱跑。他爸的面容还是那样肃穆,仿佛正在呼吸,黑白照片对他的面貌没有大的影响,反而衬的脸型更加饱满,看起来神采奕奕,完全不像是将死之人。静坐久了,他也感到平静许多,好像在跟父亲商讨未来怎么走下去,商讨他那个李后头的字该如何描绘。到了后半夜,他支着右手,脑袋偏着撑在掌背,眯了一会儿,被大伯给叫醒了。大伯提了一壶酒,两个杯子里倒满,还往桌上放下了一把剑,不知是何用意。各干了一杯后,他缓缓开口:这把剑是你爹留下来的,说要给你。李二说,我拿着它有什么用?大伯说,你不是本地的人,这个你知道吧?李二说,不清楚,我爸没说过。大伯说,你爸妈不是村里的人,他们是从外地来的。李二说,这有什么问题?大伯说,问题在于,我们都是本地人。其实我们并不是你爸的亲戚,当初你爹妈进村后,认了几个兄弟,尊称我为兄长,还有你二伯,三伯。李二说,大伯,你慢点讲,我爸是哪里的人?大伯说,这个说来话长。总之你不是这里的人,这个明白吧?李二说,明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大伯说,你爸把这柄剑留给你,说明他想让你回去。李二说,回哪里?大伯迟疑片刻说,江湖。
李二也顿了会,说,什么?大伯抽出那柄剑,寒光中夹杂着些黑点,像流传了千年的造物。他说,前天夜里,有两个刺客摸进了村,找到你爹的屋子,将他从梦中斩杀。你爹在梦中抵挡了几招,可是终究没法防住。李二说,谁要杀他?大伯说,你爹二十多年前的仇人。当初他就是因为这个来到我们村子的,你爸当初说过,如果仇人不再追上门来,他也可以忘记过去,重新生活,可是如果仇人找上门来,他咽不了这口气。李二说,谁跟他有仇?大伯说,这个我们也不了解,只知道是一户姓金的人家,你爸说,那是一家战国时的大户,借着与王室的关系无恶不作,他们养着一户刺客,能登天入云,手法卑劣,你爹一路逃至此地,才没见了他们的踪影。没想到他们还是找到了这里。大伯看上去没有疯病,李二说,大伯,你喝多了?大伯给自己又倒了一杯,说,这么多年,你爹以为忘记了过去,过往的经历就会坍塌成粉末,可你爹是痴情人,在梦里也忘不了那些前朝旧事,给了仇人寻找的线索。这些年你离开了家乡,不要以为走得远了能松懈,他们依然还在找你,他们终有一日会找到你。你要记住,不要在梦里露出破绽,不要留给他们遁入梦中的机会,睡觉的时候,要在床边放好剑。侄儿,你终究是一个异乡人,异乡的恩怨要在异乡解决,天亮以后,你就朝山下走吧,你会找到路的。说完,大伯把剑放下,喝光了那杯酒,趴在桌上打起了呼噜。一团口水从他嘴边淌出来,形成了一个小湖。
天色微亮的时候,云朵仿佛含着一粒金丹,脸颊透金光,接着开始变红。比血还要红啊。李二把那柄剑塞进背包,只塞得进一半,拉上拉链,铁剑看起来像笔直地插进了包里。他背着剑走到村口,下山的大道岔路横生,他全凭心境往前,有时听见一个声音说选择哪条道,他的双脚也极其顺从,仿佛它俩有自己的商量。走了一阵,马路已到尽头,前方尽是土路。他迟疑了片刻,也抬脚走了进去,想起小时候自己在这一片晃悠的场景,身形不自觉摇晃起来,眼皮也越来越沉,他揣测是酒精发威,可双腿并没有停下。一阵微醺中,看到眼前有两个人身着布衣,正迈步朝他走来,其中一个唱着:落叶落叶往下掉,秋风吹你轻轻飘。诸位欢聚小伙子,我来先唱你和调。李二走上前去,问,你们二位是从哪里来的?唱歌的那个说,你这是什么问题?我从这条路过来的。李二说,是在下冒昧了,请问这条路通向哪里,需走多久?唱歌的说,邯郸啊,走两刻钟就到。李二说,谢了。于是继续向前走,背上的剑仿佛吸满了汗水,越发沉重,半小时后,他走下了山,眼前有一片都城迎接他,青草累累处堆砌了一面不小的城墙,一直堆到三四层楼高,顶上书着:邯郸。城内声音嘈杂,阳光普照,时不时有人打量着李二奇怪的穿着,以及背上的那个包,以及包里插着的那把剑。在城里转了半刻,李二走入一家客舍,解开那个装着刀币的包裹,开了间房住下。
那天晚上李二睡得很好,令他诧异的是,梦里没有刺客,也没有父亲,只有他的身体沉沉下坠,彻底落地时,他就醒了。剑还立在床边。醒来以后,四周并没有变化,楼下有商贩在吆喝,几个穿布衣的行人走过,地上尘埃一片,不知道这里究竟是哪。李二坐在床上,伤感如酒气一样漫出来,仇杀的恩怨真的与他相关吗?他的人生因它而陡变了,此前的规划全都被打碎,好像过往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从一个地方被抛到了另一个地方,而自己却对它毫无了解,甚至此刻想起来时竟不知过去是梦境还是现实。人生中很少会出这样大的岔子,可遇到它的时候你也没有别的办法。你就是这样无知啊。李二取出那柄剑,握在半空瞧了瞧,看起来确实是把好剑,剑面倒映着他年轻又无知的脸庞。他到底是因年轻而无知,还是因无知显年轻,这也是一个问题。握着它的时候,李二好像看到了一些刀光剑影,或许是曾经出现在它身上的碰撞,可到如今依然雪白,只点缀着一些雀斑。这一刻,他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字:刃。热气腾腾,像是诈醒的父亲刚从梦中铸造的,向他抛来,他迅速含入口中冷却,李刃,李刃——渗出的血丝霎时黏在他的舌底,彻底与他密不可分。他忽然感受到一种说不明白的痛苦,好像脑袋上要突兀地冒出两根白毛,这种痛苦应该一直被父亲藏在手里,从不展给他看,可现在随着他的名字一并传到了他手上,也无法推辞。李刃面容苦涩,低声说:多谢。然后把剑收回了剑套,整理好背包,背上它推开了房门。

 |

 |

 |
范德清 |
张利利 |
汪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