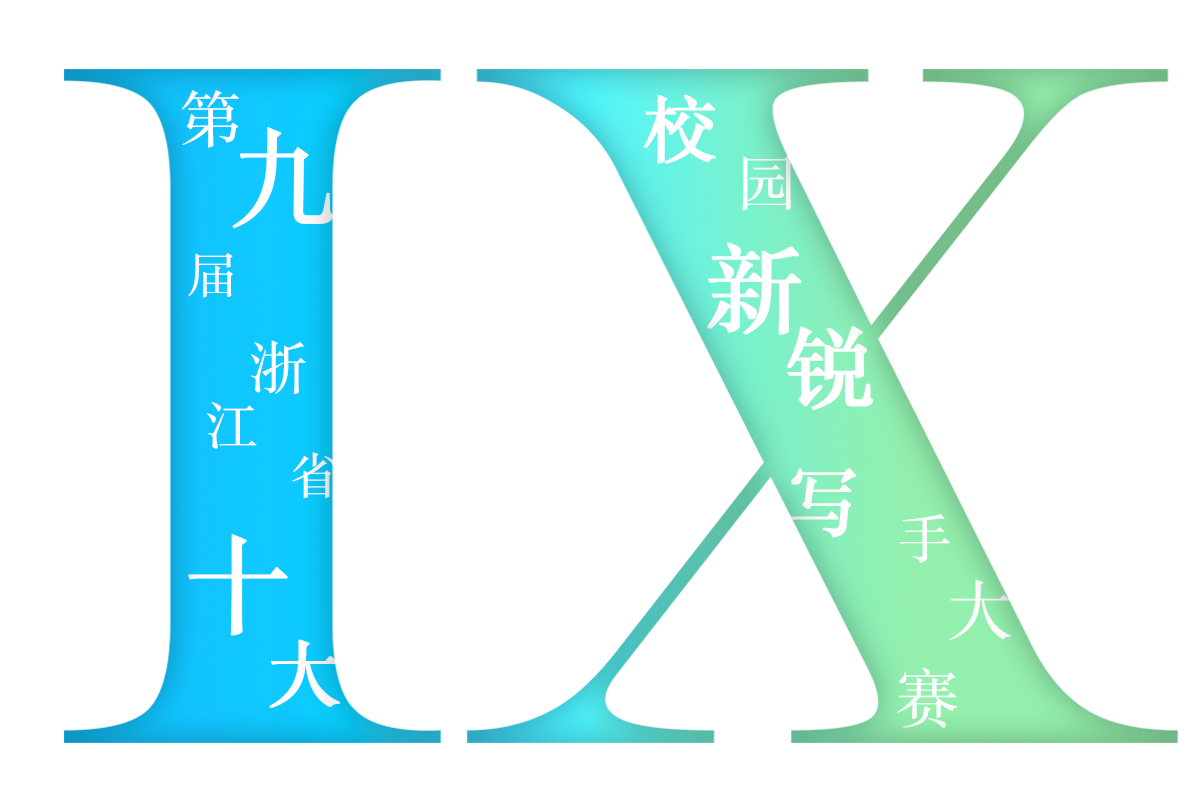黎明之前
回文序列 发表于 2022-06-30 21:51:53 阅读次数: 481夜色慢慢从地平线爬上来。他在街头游荡,一片云压在天上,另一片压在心上。荒诞的世界,整个街道空空荡荡,像精神病院深夜漆黑的走廊。
夜色和灯火在他眼前化为一片殷红。她自楼顶坠落后绽开一地鲜血,像坠落的杨梅泼洒的汁液。学校的杨梅很甜,但不会有人偷着摘。大家都等着在杨梅节那日狂欢,将鲜甜的紫红色浆液涂在别人脸上。但今年杨梅不会再熟,青涩的果实从枝头坠落,摔开一片触目惊心的殷红。
她不会回来了……他喃喃地叹息。她不会回来了。他一遍遍告诉自己,直到呜咽混着血腥味从喉咙喷薄而出。
他还记得踏入实验室的第一个月,一排排学生干劲十足,眼神炯炯,一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架势。到了期末,实验室死气沉沉,同学在作业无情的压榨下如丧家之犬般逃出实验室,留下的人个个面色枯黄,眼袋几乎垂到地上。
就在一个死气沉沉的下午,他死气沉沉地瘫在一叠教材上睡觉,在刺目的白光中艰难地睡去。醒来后实验室一片阴沉。他以为自己又被所有人遗忘在实验室了,直到打开灯才发现窗口有个清瘦的身影——想来是借着信息楼的灯光——在伏案书写。灯光晃得她眯起了眼。然后她抬头,对他粲然一笑:“醒啦?吃饭去?”他一看表,已是六点半。食堂已经关门。
售货机底“咚”一声响,然后是金属环离开易拉罐时气泡涌出的“呲”的一声。她咬着售货机里被人遗忘的老式面包,拧开保温杯喝了口水,皱着眉头看他喝着可乐嚼着薯片:“像你这个吃法,容易得肠胃炎。”
于是第二天,他醒来时桌上多了一份粗粮面包和一份沙拉,还有一杯杨梅汁。他诧异地喝了一口,还是温热的。从那一杯杨梅汁起,她的暖就刻进了他的DNA里,再也分不开了。
她对一切生命温和而温暖。他们在排球场旁捡到过翅膀受伤的小鸟,在假山的洞里捡到过被猫抓伤的松鼠。她并不在意可能存在的禽流感病毒与寄生虫,将它们带回了实验室。他还记得她在实验桌上为它们包扎,动作温柔。“学生物,是为了救死扶伤么?”她笑了:“不是。是为了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
在那间灯光忽明忽暗的实验室里他们一起解剖过杨梅,还有桂花、蚯蚓和小龙虾。他们甚至还取过栏杆上新鲜的鸟粪,就为了看看那鸟没有消化的种子来自什么果实。他认为是构树果实,而她坚持是杨梅。简陋的光学显微镜并不能为他们的辩论提供公正有力的判据,而辩论的最终结果是他去学校超市买了一篮杨梅。两人就着流出铁红锈水的水管大快朵颐,紫红色的汁液欢快地染上了发黄的水槽。两人头顶上的“实验室公约”脱落了一半,剩下半块勉强支撑在墙皮上,一滴紫红色的汁水溅在发黄的字迹上:实验室里禁止用膳。最后他们餍足地靠在实验桌上,看着对面计算机教室透出微微的灯光。实验室的灯忽明忽暗,而她的笑颜亮如白昼。她崇敬遗传学鼻祖孟德尔。他将孟德尔调侃为“豌豆射手”时,她嗔怒地拍了他一下,眼里有流光闪烁。
那样的光在她眼里燃着,如同她对孟德尔的崇敬一般长久不灭。他还记得去年联赛前一天,她虔诚地在孟德尔的画像前供上一盘豌豆,深深一鞠躬:
“孟德尔祖师爷,愿您保佑您忠实的信徒和她所爱的人联赛大吉。”
她的声音在空荡的走廊里回响,更显空灵。然而——竟是再也听不到了。
在孟德尔的画像下他紧紧地拥抱着她,她闭着眼,看不清她的表情。她浅红的头绳上有两条丝带垂落发间,像黎明时的薄曦,像她。
然而孟德尔祖师爷没有眷顾她,她的眉梢染了一层阴翳。很快,高二难度陡增的考试让他猛然意识到竞赛让他落下了多少课内的知识。他退了,向高考妥协。然而她如刺客怀着死志一般宣告自己不会让步,于是他搬着一叠《高考五三》来到实验室,看着她在大学教材的知识点中浮沉。黄昏时她在信息楼投下的灯光中向他展颜一笑:“谢谢你,陪伴了这个年级唯一的生竞生。”
对于这“唯一”,他敬佩且珍惜,而班主任老黎似乎却不这么认为。老黎是个开明的老师,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老黎默许了他们略微越界的甜蜜情愫。而老黎对她下滑的数学成绩并不那么宽容。一次又一次,他听到老黎苦口婆心地劝她退一步,专心课内,专注高考。她只默默点头,整个人陷进老黎高大身躯投下的阴影之中。
秋天的寒意在蔓延。她的长发日益枯黄,黑眼圈一再加深,重重涂抹着她的憔悴。她的唇一点点失去血色,脸色由蜡黄泛青。他抱住她时总感到她轻轻的颤抖,但她不承认。“会好的,马上会好的……”她轻轻地说,一遍又一遍,不知是安慰他,还是试图说服自己。
窗外,构树的叶子转为枯黄,再从枝头旋转着飞起,轻轻地坠落。她依旧会在他睡去时为他关上实验室的灯,可她似乎开始畏惧光明。当他在黑暗中醒来并摸索着打开昏暗的灯,她不仅眯起眼,甚至会猛地蜷成一团,然后极慢地松弛下来,像一块弹性不是很好的海绵。
后来她不对他说“会好的”了。或许她也放弃了。当他把她拥进怀里,试图用自己的体温平息她的颤抖,她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联赛考完,就能好好准备高考了。”他悲哀地凝视着她失神的眼睛,悲哀地叹息:这具骷髅似的躯体的主人,竟只是一个还没有开始准备高考的高中生。
她拖着骷髅似的身躯,在每个黎明亮起前打开书。书里有一切她渴求的生命的真谛。而他默默地看着她,从她眼里他看不出一丝欣喜。或许,他想,是因为书里没有一条知识点告诉她,她的生命的真谛,是什么。
夜色深了、浓了,又似乎要在雨中化开。他感到他也要随夜色一起消融了——被夜色包裹着无声无息地消逝。她没能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他也没有,也没有人能记得他存在的痕迹。他突然意识到她在黎明亮起前打开书的目的。或许不仅仅是勤奋所致,亦是……在黎明前,她必须找到证明自己活着的痕迹。黎明……实在是太亮、太空白了。他发觉,她对生命的疑惑和热情,在白昼下和周围人的麻木形成了更鲜明的对比。他发觉,不止在他眼中——也在白昼下的所有人眼中,她的轮廓,更清晰地暴露在人群的背景下。
运河里的货轮缓缓驶过,劈开的水波在船后愈合。雨更大了,愈合的水痕上泛起波纹,被无尽的鼓点反复搅扰,不得安息。雨声更响了,完全盖住了他的脚步声。他觉得自己的存在化为了雨中一条弹幕,而雨的千万条弹幕将他裹着,闪过黑屏的背景,生命的背景。
如何证明她曾存在过?因为她死了所以她曾活过?他不禁怀疑世界在他的臆想中扭曲了,而他通过小孔向外窥视,窥到了一切颠倒的事实。雨落到他发间、肩部后溅起,是否说明他形体尚存?可是雨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义无反顾坠向地面,形神俱灭又怎能证明他曾存在过,温热过?或许他会失温而死,可是躯体顽强地对抗着寒意。此刻他深刻地理解了生物老师说的机体自我调节:神经和体液违背了主人的意愿,顽固地使灵魂所依附的躯体正常运作。或许他会变成磷火,那应当算一种光。物理老师说光具有波粒二象性,那此刻他是波还是粒子?或者,是物质世界被掏空的一块人形洞?
满天满眼的雨水将他的视线模糊,冷白的街灯遥远如星星。他觉得自己从未离星星这么近。星星的光芒将他围住,他被黑夜的漏网之鱼包围了。雨一直下。他已辨不清是雨从天而降,还是自己正在融向雨中。雨声中仿佛有一个声音反复在他耳边叹息:“我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知道。”
夜色在荡开,天色转成了不那么纯粹的灰。黎明要来了。那个黎明寒气森森,她纤瘦的身躯倚在窗旁。一片枯叶缓缓坠落,宿舍楼旁的青石板路溅起一片殷红。尖叫声割开清晨的雾气,救护车的呜咽声中太阳没有升起。他在油烹的煎熬中等待,一天一夜,又一个黎明,太阳不再升起。阴冷的雨滴中出殡的队伍迟缓地移动。当她瘦弱的身躯在传送带上缓缓进入火化炉时,老黎隔着玻璃窗无声地痛哭,一米八的身躯颤抖成一个凄怆的黑影。天地间寒雨如刀,一把把黑伞护着她安睡着的檀木盒子进入公墓,护着她长眠于石灰、丁香和水泥之下。
在她的头七,他梦到了她。梦里她笑容明艳动人,浅红的头绳在晚风里洒脱地飘荡。“为什么不退?”他听见自己发出嘶哑的声音。“退?为什么退?我用生命证明我对生命的爱,不好么?”她轻松地笑着,声音空灵而渺远,却清晰地回响在他耳边:“跟我走吧。当你的生命结束,你才能真正认识生命本身。跟我走吧,生命的尽头有一切关于生命的答案。”
雨中的寒意渐浓,冰冷的雨烫到了他,使他炽烈地灼烧。他举起双手护住自己,在滚雨的舔噬下如堕油锅。他嘶吼着想要剥离自己的灵魂,声音溶解在雨中,像极易溶的溶质被雨声啃得一干二净。他在灼烫的雨雾中彷徨,雨强势地落在他唇上。恍惚中他又看见她,那么近。雨将天地间的浮色洗净,只剩她白得透明的脸。世界回到了原点。她的唇带着极寒中仅有的温度,她的唇是无尽虚空中唯一的色彩。她脸上细细的绒毛在雨中愈发清晰可见。她的深黑瞳仁无限靠近,宇宙在那至深之处诞生。
他感到灵魂从绝对零度中挣脱了束缚,自唇部起,血液开始在躯体中流淌。然而雨依旧舔着他焦枯的皮肤。他觉得自己的肉体在萎缩,或者在雨中吸水涨破然后干涸。可是思维像蜘蛛群一样向虚空中蔓延。在无尽却不存粹的黑暗中,他想起曾经蜷缩在屋角——黎明将来之时屋里最后一角黑暗。他想象自己是个蓝细菌,在黑夜中呼吸进化。天在亮起来。他徒劳地将双臂挡在头上,却无法阻止阳光进来。太亮了,太寂寞了。什么都明明白白的,一丁点空隙都没有。我该消失了,他想。黎明要来了,一点空隙都不会给他留下。
思维奔涌如寒武纪大爆发,坠落的杨梅,孟德尔,枯黄的构树,还有她——统统不重要了。在灵魂爆裂的痛苦中,他奋力地想要用嘶哑的喉咙发出生命的余音,最终却只是一声叹息。

 |

 |

 |
范德清 |
张利利 |
汪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