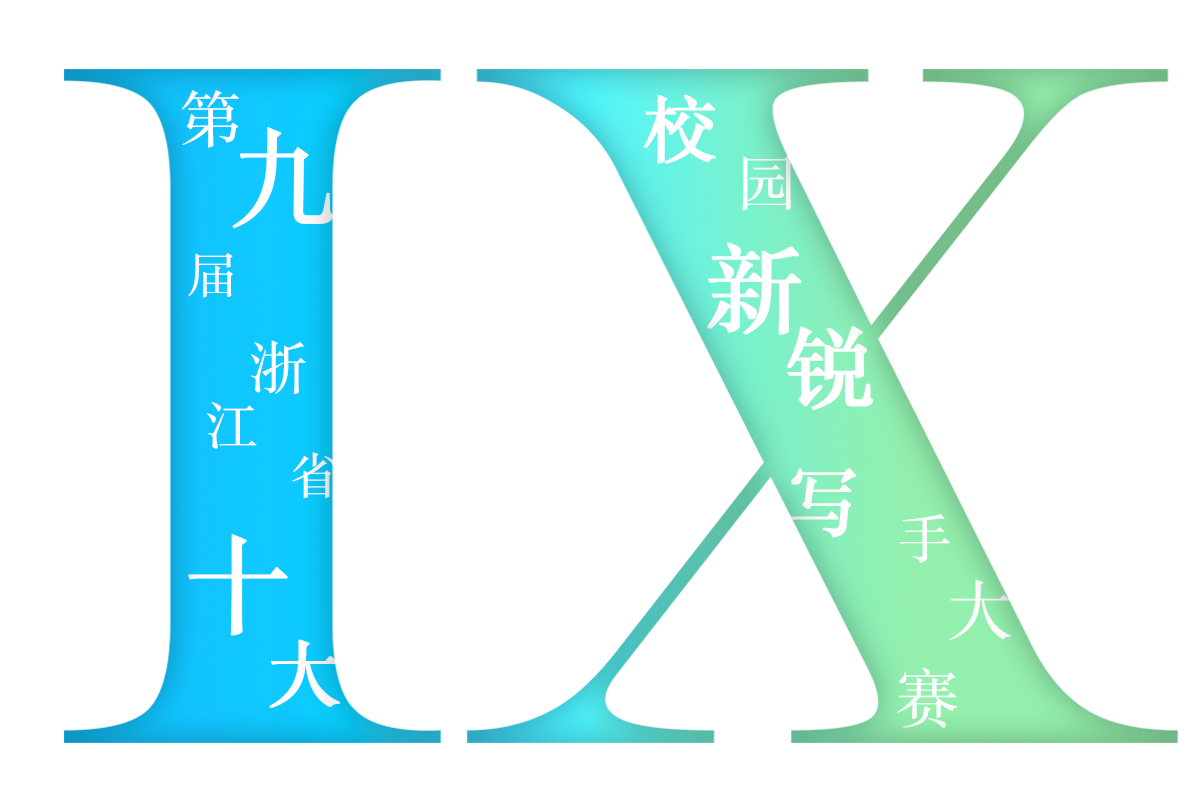雨中散场
镜花魂眠 发表于 2024-05-04 23:57:29 阅读次数: 69夜晚,伴随着铃声的愈演愈烈,晚自习第二节课开始。
于学生而言,上课铃是为数不多无法屏蔽的事物之一,瞬间将我从题海间抽离。我先是背靠墙壁伸个懒腰,环顾一圈在铃声中逐渐落座的人群,转而埋怨地抬头看向公告栏上方还在响铃的音响。我忍不住深吸口气,试图缓解刷题带来的的沉闷感。
沉闷并没有缓解。四周充斥着空调开低温产生的阴冷湿气——就像一个深潜者从海中刚刚冒头,还没来得及深吸一口气就一头栽进另一片汪洋。我悄悄拉开窗帘,双手用力将窗户开个小缝。顿时,窗外湿热的潮气与室内同 样闷热的空气对撞。一股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气息向正对着窗缝的我涌来; 不同于闷热的叠加。一种突如其来的清新。
在被副热带高气压带和东北信风带交替控制的淮南沿海城区;每当春天走向深处而夏天却迟迟未踱步,四周中空气总会裹挟着密密层层的热浪。这种感觉,在下午两三点,晚上八九点尤为明显;这俩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若把下午两三点时比作一个人全身毛发竖起、怒火中烧后由内到外逸散的燥热,晚上八九点则是燥热退去后的阴翳所带来的闷热。相较于前者所带来的燥热,后者的闷热并不会轻易被吃棒冰等降暑措施揶揄。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我早就习以为常。
窗外是初中楼,与高中楼正对。远处,十字路口上川流的车灯在铁栅栏和铁树的遮挡下若影若现,勾勒出两条白练。有的是接学生的家长,有的是离校的老师,有的是骑电瓶回家的叁俩学生。还可能是下晚班的社畜。还有远方不断跳动着婚庆祝词的楼灯。这是除了一排排整齐的教室外唯二的亮光。不过我很快关上窗,将窗帘拉上。副校长曾多次在学校晨会最后的党八股中反复强调,晚自习严禁一切与学习无关的内容。没过多久,我就再度陷入稀拉的笔尖摩擦声中。
不知过了多久,莫名有人轻拍我的左肩,我不予理会,紧了紧握笔的手;拍打停了。稍顷,拍打再次出现,且更为急促。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转头发现竟然是班长。她右手毫不避讳地翻弄着手机,左手不断开合示意我起身。我起身刚想出言提醒,可她把我椅子往里一推后直接将我挤开。这不像她,我心想;脑海顿时有些卡壳,想不起啥时候得罪了这尊瘟神。我抬头想和她解释,可抬头的瞬间,我愣住了;她浑身颤栗,趴在窗户上的身子也不由僵硬,往后跌几步。
“有人跳楼了。”
声音不大,却让班里原本尚存的窃窃私语瞬间安静。我一回头,直接迎上无数炽热的目光,瞬间面色赤红;一看来不及回去,直接蹲下身,随后闭上眼睛,脑海里一片空白。班里几乎所有人都出去了;我成了少数,至于原因,大概是出于对死亡或者人流的恐惧。我呆呆地坐在桌前,没了思考题目的心情,淡淡地回味着“跳楼”二字和自身的距离。直到听到走廊上有人喊:“巡查老师走了!”,我才敢合上课本下楼。
楼道里没有亮光,甚至连声控灯都没有。走到半路时,我听到警笛的呜呜声;随着警笛声响起,我犹如一个迷途的羔羊,在沼泽中陷落,下沉,下沉,再下沉,直到身体的最后一寸融入夜色。
一群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初中楼前。我站在高中楼的架空层远望。警察刚把车停在校门口,就快步跑来拉警戒线,用防爆盾牌驱散人群。楼上也是一排排的人,低着脑袋往楼下看。在楼道的尽我隐约看见伸出一只端着手机的手,不知是在拍照还是录像。直到我走向熙攘的人群,才发现已经下起小雨。没有一个人打伞。
“我记得在五楼见过她。”
“隔壁班的。她好像是出轨的那个,嘻嘻。”
“出轨?”
我回头,两个女生与我擦肩而过。我没有多言,站在人群的最外沿,踮着脚努力往里看。
“诶,那边有个人。”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闭嘴,她家长来了。”刚刚忙于八卦的女生也被边上的人打断。
来人比较年轻,像是女孩的母亲。她脸上化了妆,穿高跟鞋,大概刚从比较正式的场合赶过来,嘴巴不时翁动,像是在念叨些什么。待到她将我从身前挤开时,我才发现她的妆花了,呈水痕状;可能是因为下雨,因为流汗,又或是其它,我心想。人实在太多,高矮胖瘦都有。“同学,让一让。”“那位同学……”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不过人们大多都选择避开。突然,她一个没注意,被绊倒,左手压在地上,原本在右手的手机因惯性被抛出。手机先在空中划出一道银弧,随后砸在地上,翻了好几个跟头。地上满是屏幕的碎片。碎片在地上闪了闪,不一会就被四周的阴影吞噬。雨势有些大了,偶尔落下几滴大颗的在我的额头、手臂。我撑开伞,许多人看到后也照做。
在她倒下的瞬间,以她出现大块空地,一时间没有人扶她起来。她闭上眼睛,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脸上的妆容彻底花了;宛若另一具没了呼吸的尸体。最后是警察将她扶起,泥水从她的裤脚一滴滴滚落到地上。她木讷地往前走,直到看见尸体,她也没有说一句话。尸体脸朝地面,手脚扭曲地向上九十度弯折;血肉模糊,我分不清男女。一根原本就被压得几近折断的树枝从树梢落下,落到尸体边上,没有发出一点声响。当我在此将眼神转向那位母亲时,两行清泪从她的脸上淌下。
很快又有警察从车中取来担架和白布,将女孩送到街道对面的法医鉴定处。地上留下一滩血渍,在雨水的冲刷下仿佛被重新唤醒,时而暗沉,时而鲜红。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人们的思绪才被渐渐唤回。有的人回去上楼拿书包,而有的人早就将书包背好站在校门口。我走在去校门的路上,发现今天离开学校需要排队。我提前用手机将车打在十字路口,在路边警局的安保处看见校长和副校长摆着谄媚的样子和警察赔笑。我没有多呆,因为副校长是我的语文老师。
一路上,我想起自己也曾多次有几近跳楼的时日。我曾在小学因为父母离婚在学校无论走到哪里都被同学指着错号捉弄、嘲笑;曾一个学期在音乐课上被同学编歌谣辱骂,我忍无可忍回骂一句,老师让我写检讨。我最美好的回忆是在初中。到了高中,我多次被人在寝室围堵,最严重的一次,我躲在有监控的自习室直到凌晨。不过幸运的是,我苟延残喘下来了。我也天真地向老师告状,但老师头也不回地送了我一句:别人为什么不会。这些不谋而合的回答,从小学到高中,从未改变。老师是如此,家长亦然。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求助;我冥冥间察觉如果再问下去我也会如同这般,在他人向我求助时发出“别人为什么不会”的回问。想到这,我瞬间打了个寒噤。
一阵滴滴的督促带着明晃晃的车灯让我习惯性地收伞,拉开车门,随口报出手机尾号的最后两位。在拉开车门的空档,雨滴密匝匝地落到我身上,让我原本炽热的身躯得以缓解。
车内没有开窗,窗外不断有汽车和摩托飞驰而过,闪过道道白芒;时而阴沉暗淡,时而闪烁夺目。手机上时不时弹出相关的照片和聊天。我合上手机,慢慢将车窗摇下,出神地望着川流的人群,眼神跟随他们身影在我的视线里出现、离去。一个个人,如同天上飘泊的雨水般,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这场大雨中慢慢散场。

 |

 |

 |
范德清 |
张利利 |
汪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