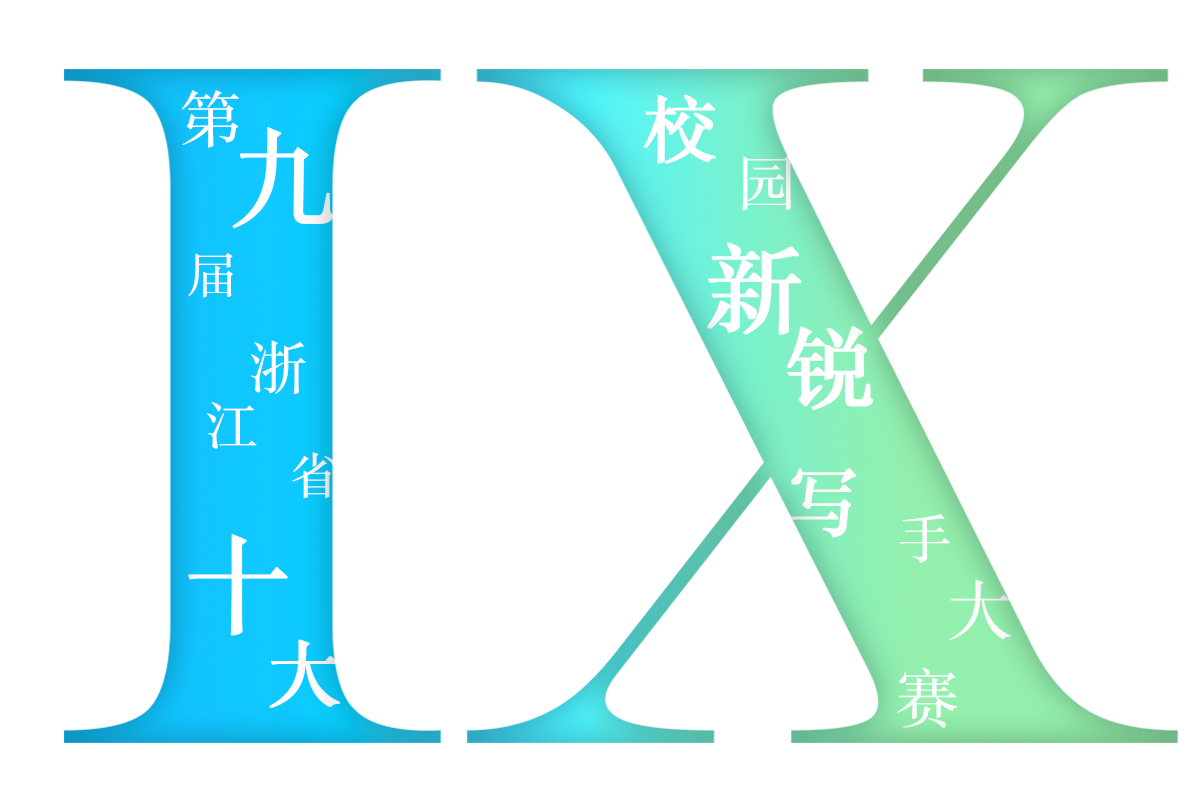新生与老去
何人见我如归乡 发表于 2024-05-04 00:06:31 阅读次数: 51八岁时的一个傍晚,天空正微微深蓝,那时我坐在大伯开往镇上的车上,途中必须经过一道桥。那座桥将这边的村落与那边的城镇联系起来,在那个傍晚,我清晰地记得微凉的晚风像是丝绸一般吹过,萦绕在脸上,蓝色的幕布下,我看到缓缓流淌向远方的江水,尽头是隐约连山。
长大之后,江水的名字恍如土地的基因般开始生长在我的脑中——横阳支江。江水的连绵像是植物的茎脉,扎根蔓延在这片土地,由此将所有的养分吸收。在15 16年时,家乡开始大建各类设施,建商场建体育馆。放学路上,我总注望不远处那尚未完成的工程,它们在落日阴影下显得深暗又空洞,似乎摇摇欲坠扬起满天烟尘的比萨铁塔。转眼就是另一岸,那里更显荒芜。行车过去,路边堆满了房屋拆迁后的碎瓦残砖。在微微隆起的地带,移动房肆意丛生。晾晒着贴身衣物的竹竿与遍阶滴下的水,零落的叫卖声与通向乡村深处的分叉道路。每个落日燃尽余晖的黄昏,我都在这江水的两岸看到截然不同的样貌,仿佛一带是将死未死的过去,一带是将生未生的未来,如同森林背阴迎阳的两面。
这种定义不会出生在尚且年幼的脑海,而是在某个长大的瞬间悄然而至。在十岁出头的春天,我正从老家骑上镇去,爬坡时愈上升愈发困难,直至顶端,我方敢松懈我一直紧绷的神经与肌肉。而就在风里微微颤抖着呼吸的瞬间,我才发觉我正在过去的最高处看到这新生的明天。那是一座接着一座的高楼,潮流不息的车行,以及远处更加浓密的绿植。袭来的东南风胡乱地抹在我的瞳孔,眼睛感到酸涩发胀。启示性的字句即刻印如入脑海。
“在这片土地上丛生着新生与老去。”
事实上,这番字句太过宿命化我的家乡。我该笼统一点,“我们的所有记忆都饱含着新生与老去”。
家族来说,新生无疑指的是我。年幼的我饱尝了家里人的优待。在六岁那年,我的一位阿太去世。那时我对死亡没有概念,是在父亲的怀抱下登上山去的,只记得微微燃起的火。山上轻轻的风将烟吹得弥漫,并不好闻。长大些许,我才真正挖掘到那个慈祥老人的记忆。父亲说,他是这几代家里面最有出息的人,是大学生,应该正是新中国成立时候的。母亲说,当初我的名字也是他取的。父亲母亲陪这位老人坐上了一个下午,最终夺定我的名字。我记忆里还有他为我弟弟取名的记忆,他缓缓地从木阁子抽出很大一本的康熙字典,在上面一个字一个字地徘徊,定夺。而那现在传到我的手上。接下来直到十一岁时,我生命里又一位老人死去。是我母亲那边的阿太。做了一辈子的老师,退休后喜欢打打麻将。在阿太未死之前,一个午后,暖光烂漫,我已悄悄地沁出汗液,迷糊中,阿太一直以他那双老去的仍然清澈的眼打量着我,最后要走时拍拍我的肩,让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好好生活。他的死突如其来,在一个晚上躺倒,隔天早上就安然离去,没有多余的病痛折磨。那时我被拦在门外,不让进去探看,大人们都进去纷纷揭开白布,流下泪来。最痛心的是他的老伴,跪倒在地上,以布满皱纹的手似水般抚摸他的逐渐变硬的面庞,嘴里微微哭诉。大人们说,这就是造福积德的表现。人好好活了一辈子,造了功德,死去时就没有多余的折磨。
所言实真,他和他的老伴都极为优秀。也就是我的另一位阿太,明年就即将九十,而如今尚还硬朗,让人看不出岁月与她有多少冰冷的着痕。听母亲说,她年轻时捡到死去的人的骨头,便带回家毫不忌讳地烧作骨灰,承在盒中,又点上香烛放在案上。一种近乎传奇的故事。或许正是这种善良使她如此健康,在耄老之年尚能到处游玩,闲来执笔书法。
浪漫主义诗人 洄游季节的鱼类 以及趴在草原上边睡懒觉边远望猎物的狼。这三个词可以概括我的初中三年。初一一年我享受生活,享受着新生与希望感。成绩无需担忧,一个学期的语文作业都没有去动过,上课也与同学聊天,或趴在桌上写我的小说。或许是那一年太过灿烂:我品尝了恋爱的味道,在大雨倾盆时刻狂奔,也在大风中静立,感触它柔丝般滑过我的身躯,以至于接下来的日子我只得改变天性通向学习。初二我徘徊在优秀边缘,一半躺平不愿改变,一半不甘如此,暗暗奋斗,好比一条不断回归的鱼。初三也大抵维持,但多了许多迷茫,在专心学习以外的更多时刻,我在犹豫地望向未来,仿佛下车后在车站探头寻找下一班车的游人。网上常说一句“青春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确实如此,青春就是一场不断重复着新生与老去的霓虹灯秀。好像从温热的水池中挣扎上岸,身边人都说自己浸泡在不清不楚的失重感中,在荒草丛中遥望新生的太阳,在自己心中点上老去的日下月上的景色。对于大多的我们,都没有能力在这个不安年代承受新生的冲击与消去的遗憾。
去南京时,记忆最深的是梧桐大道。还未睡醒时行走其间,那连绵高挺的梧桐树早已在初日照耀下投下不绝的微微透绿的影子。暗动的气流与树的沙沙作响,像是一次冷静的接吻,令人脊背扩张出新奇感。走在其中,一半是光,一半是影,我竟然在影中感到异样的忧戚,又在光中感到生机。它们交织在一起,恍若两条若即若离的河流。当时我并未搞清楚为何受动,如今才意识到,我是在感触那种纯粹的自然感。那静静对立的乐与忧,新与老,就糅合在那光影里,我有种预感,这梧桐大道如此地壮观,简直遮天美好的景象,许是就是待我来感受它的意义,好比史铁生与他的地坛,它说,“新生与老去的概念将在你的记忆中留下痕迹。”
为什么会喜欢陈绮贞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喜欢沉浸在情绪化里,包括对新生与老去的感触,这也是情绪化的定义。听她的歌泛起的情感,像是在身周冒出了一个个富有韧性的泡沫,无法戳破,那不是阴雨连绵,而是一种适应性的行为,由此我可以感受到记忆的着痕。五一那个天气晴好的下午,我开着车疾驰在这片土地的每条道路上,环绕了一整个县。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所生活数十年之久的地方,还有许多我不知道之处。彼时,耳机中正循环播放着陈绮贞的歌曲。在那乱舞的风中,我为我凝结上一层薄膜,身体逐渐发烫,升温。我在歌与风声中看到县城边缘地带,它们被命名为老街,是旧时代的产物,已然不再繁华,然而仍然有人定居在那;我也回到农村开了一遭,每家有每家的炊烟,每村有每村的闲话,它们都在享受着这种对立的,老去的,安宁。陈绮贞正在唱“一步一步走过昨天我的孩子气。”温柔的歌声却在此时显得滚烫,一种时代和时间感迎面而来——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常常被既视感包围。在某个瞬间蓦地停住,思索着一幕是否已经发生过,是否已经发生在我的梦中过。认清时的想法,像是从苦难中解脱,“原来我是活在一种重复中吗?”——这一刻也是既视的一抹,然而这一刻我并非愣住,而是眼角湿润。在那变化色彩的景致中,在那急促的风里,在我用力拧动把手的刹那,我自嘲般地想起所有有关老去与新生的事:明日与旧日 印象与对视 死亡与出生 回忆与现在。太多的记忆提醒着我去观望新生与老去这一概念,像是长路上驻足的行人。我最终唱了出来
呼吸 这一秒的空气,
还有多少回忆,
藏着多少秘密,
在我心里翻来覆去。
过去并未消失,而未来已经存在。我意识到新生与老去鲜明地共同存在于这个世上,仿佛一种刻意的警示,一种对比的留念,一种恳求勿忘的念头,一种夹杂世间万物的表面。
开了很久的车,直到反应夜晚将至才匆匆回程。在归途上,我偶然又必然的经过那座桥。一切的喧嚣和灯火都在那一刻与我若即若离,似乎可以游离的鱼,摇曳中我又看了一遍横阳江水东流,携带着往日,它仍然静静地流淌,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变意,似乎要坚定执着地流向我的尽头。其实真正令人注意到这两者的是时间,在不经意间原来每个人都过了那么多年。
我该感谢我的记忆,那就让新生与老去肆意生长在我的一生。

 |

 |

 |
范德清 |
张利利 |
汪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