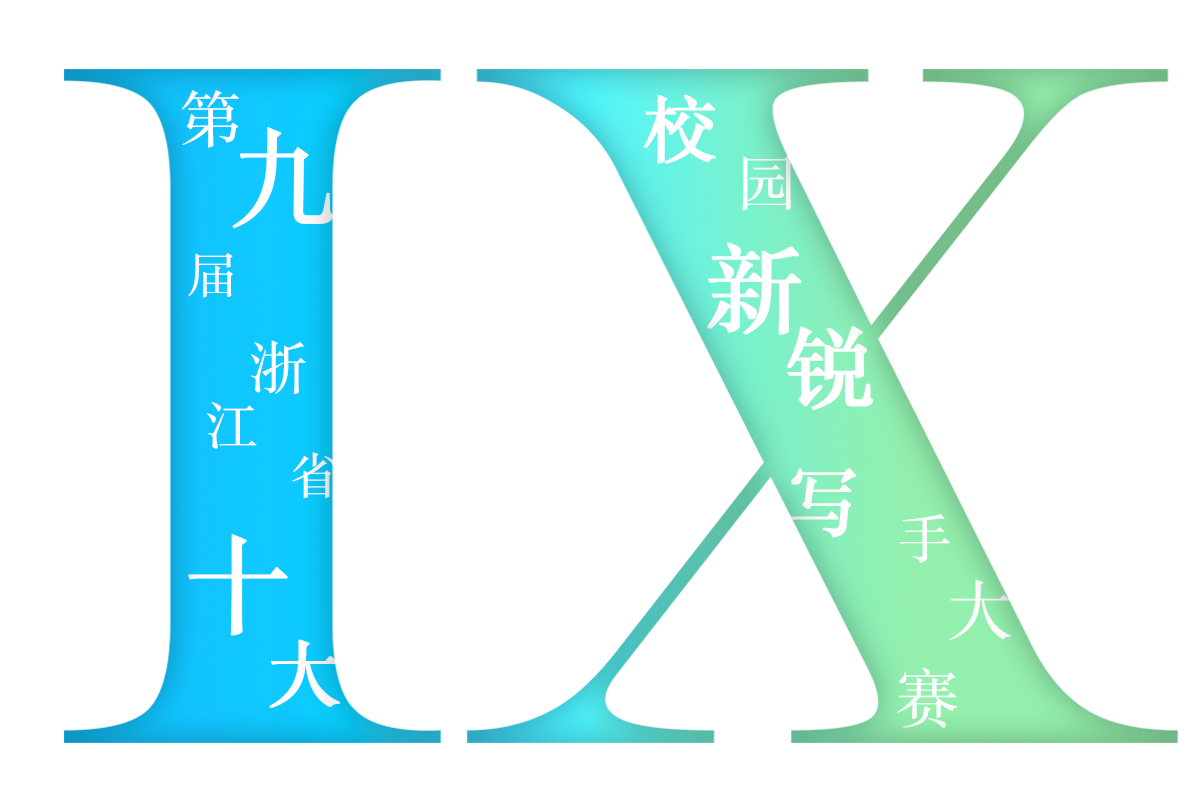窗外的世界
奈布嗷呜 发表于 2022-10-01 18:04:36 阅读次数: 5窗外的世界
太阳放晴了,我抱着马克笔,走过走廊。砖墙上微微熏着黄晕,发丝间,也拥挤着阳光。慢慢踏进美术教室,我挑了个角落坐了下来,铺开画纸,拿起铅笔,用笔头慢慢敲着画纸,眼望着窗外,感受午后的晴空。“Hi!”老师挥了挥手,踏进教室。我转过了头,也微笑着回复了。
同学们陆陆续续走进教室,上课铃响后,美术刘老师讲起了画画的技法。粉笔嘀嗒地在黑板上敲来敲去,线条被流畅地滑落在墨绿的黑板上。我放下笔,看着粗糙的黑板。
“今天的课堂作业是以‘外’为主题画一张画。”老师放下粉笔,微笑着看向我们。那微笑是一条圆滑的慈祥的曲线,如彩虹般荡到我的眼前。再看着教室的玻璃窗外,郁郁葱葱,绿叶在微风中跳动着。那是生命在欢呼。阳光呢?我又眯上眼睛,斑驳的光影晃动着,眩晕了我,再睁大眼,那些小精灵呢?我惊呼,弯下身子,看到窗台上,阳光从孔中倾倒下来,温暖的鹅黄,交织着孔外碧绿的叶片。他们正淘气地躲在这个小世界里,却又热情地邀请着我们这些巨人与他们舞动。我贪婪地窥探着,阳光交织在我的发丝上,又越过脸庞,落到地板上,热情地簇拥着围成一个圆。
我知道我该画什么了!我拔开黄色马克笔的笔盖,细致地在白纸上涂抹上阳光。当笔尖轻轻地踮起脚又落下来。光晕便定格在这一小小的白纸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像是盛开的花瓣。我透过这张白纸,将我看到这个梦幻的大世界一点点映衬到小小的画纸上。
狭小的教室中,我拥挤地淘着画笔,却宽敞地涂抹着。电扇聒噪地叫唤着,却奈何不住这个桥梁,从狭小沟通到宏大。
铃声响起,我惊讶地抬起头,眼前是早已是空虚虚的教室,同学们一个个走开了。椅子颓废地摆在桌旁。只剩下这个空洞的教室,但刘老师却还站在讲台上。我急急忙忙收拾起画笔,抱着画纸,也离开了教室。“老师再见!”我回过头。老师笑了笑,又是一个没有棱角的曲线,就像光晕的弧一样,无规无矩,热情便溢出线外,进入我的心中。
下节是数学课。数学方老师拿着一个巨大的三角尺,一进来便是将尺子按在黑板上,画图。三角形,正方形一个个棱角分明地刺向别的图形。线直直地绷紧着,不敢喘出一声大气。他们仓促地想要依偎在别的线条上,却又被排斥开来。孤零零地楞在粗糙的黑板上。课紧凑地开始了,也仓促地在线条中结束了。我茫然地望着胡乱堆砌着的几何符号,在电风扇吹出的热风中凌乱。
放松一下吧!我心想着,从抽屉里掏出被压得严严实实的画纸,看到那抹明亮的鹅黄,貌似所有的线条都会被融化,变得温和,润滑。那黄色不断地溢出纸张,渲染住整个教室,哪怕只有几十平方。我再次拿起马克笔,低着头,想象着窗外那跃动的生命。枝干从画纸中伸出手,正热情地等待着与我拥抱。我准备凑过去。“润光,你在干什么?你因为画画丢多少分了,也该多刷刷题了!”我停住了,低矮的身躯胆怯地望向高大的身躯。“我知道了。”我缓过神来。“嗯。”老师把尺子搭在我的肩上。“你也该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你拼搏的足迹吧!这是培优班的几何作业,你也该试试。”他把好几张白纸凌乱地洒在我的书桌上。整理完桌面,方老师早已抱着尺子迈出了教室。我舒了口气
刚想拿出画纸,继续描绘,我发现纸上压了一张便签。那是学校接下来的日程,下下周二就是期中考了,附了我上次月考的成绩。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再看向画纸,碧绿已经在黄的映照下枯竭了。又看向练习册,黑字正在白的映衬下不断侵蚀着每一行每一列。十几厘米宽的纸张踏满了字符,像早高峰的地铁,大气都无法喘出一声。
你望向宏大,他则会伸出手邀你成为其中的一粒尘埃,却享受着整个世间的怀抱;你触及狭窄,他则会条条框框包围住你,冰冷的直线严肃地守护着目标的尊严,推着你跑向现实的奥秘。
我塞回了画纸,拿起圆珠笔在题目上挤压着笔头机械地往下写去。
蓝天搁浅了,灰色的云一点点蚕食着这份明媚,接着是雨,溅落在地上,绽放出昙花,却又在一瞬间枯萎。整个下午,我泡在了自习室,为了两周后的考试。打开书本,又合上书本。我惊讶于题量之多,咽了一口唾沫,笔在草稿纸上推敲起来,划过时间,划过爱好,停留在目标前。
晚自习马上要开始了。我走出自习室,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撑起雨伞,踏进雨帘中。满天的丝线随着风向伞边飘动。后来却打起了结,如一黄豆般,索性砸向伞上。我疾跑起来,可那雨终究是躲开了雨伞,砸到了我的书上,白纸深了,白纸皱了。
狼狈地回到教室,我急匆匆摊开作业本,笔迹有些糊了,晕到别的题号上,深邃的黑暗一点点渐变为黯淡的灰色。这一次,我没有见到棱角,只看到自然强势地冲破这些条条框框,但又柔和将这些字舒展开来。我的眼神恍惚了一会。赶紧掏出那张画纸,小小的画纸中,我又窥探道那份活泼,是嘹亮的声响在无尽的热爱中回荡,再一次渲染着心中的世界。枯黄中,绿踏遍原野,傲慢地向上攀登。那硕大的窗中,阳光泼落了出来。
一周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又来到了美术课。抽屉里,那张画纸早已被别的教辅压在了最底下。慢慢搬开这些书本,我再一次取出了这张纸。手轻轻地抚摸着粗糙的纸质,眼仔细地凝视着细致的迸发出来的世界,明媚的阳光温暖着我的心,我终于又可以自由地掏出马克笔了。当笔墨一点点渗进每一点纤维,滋润着这愈发干涸的树木。眼里,只有这张纸,他是我唯一的世界,是我心中的广阔的原野。我要无私的去浇灌,看着阳光再一次律动。
准备走出教室,那硕大的身躯又站在了窄窄的门口。“为考前复习,美术课由我来代课。”方老师拿着三角尺咚咚敲了下黑板。班里一片唏嘘。我皱起眉头,看看窗外,对面的美术教室寂静着,风扇吱呀旋转,课桌零散地被推到了教室外面。
美术课是不会再有了。
天还未放晴。乌云笼罩在树木的上方,外面没有一丝风,树叶颓落地打下疲惫的身躯。只有教室里吱呀的风扇还在吱呀旋转。它是想制造最后一场热闹吗?可除了老师讲课的声音和同学们的翻书声,风扇又带来了什么?狭小的世界里,他又拂动了什么?
窗外的树叶经历过稚嫩地牙牙学语和蹦跳着的茁壮成长,他们也要经历那个为了目标而放弃爱好的时节。于是黄绿与嫩绿消退了,阳光不在树叶上停留,而是匆匆赶去下一个地方。树叶变得苍翠欲滴了,但叶脉的褶皱也就明显了。他们已经知道阳光不过是为了完成工作,才在这叶片上驻留欢笑。于是那褶皱便愈发明显了。
课继续上着,我缓过神,盯着黑板。我必须锁上这座旷野。我抬起了头,眼神却耷拉下来,然后又急忙撑起,想让自己的注意力全部注重到这硕大的黑板上。这张画纸只有苍白的字迹,那是树叶与枝干花尽无数个日夜培育出的花,可没有了曲线,只剩下冰冷的骨架。我不知道他以后的样子,我只知道这是小世界所做的画。是我必须所做的画。
扭过头想要借圆规继续做题,却再次看到了黑色方框外那个原野,里面挤着绿叶。阳光跳动着,照向昏暗的桌角。不能出神了!我警戒着自己,立马拉上窗帘。脑中一片空白。再摇摇头,脑中还是虚无的,但眼前还有这黑板,我便马上记起来。
期中考结束了,这次的我有了极大的进步。当我欢快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整理着抽屉准备放五一假期,闲暇时望向窗外,阳光从窗中按不住的迸发出来,温暖的鹅黄,交织着孔外碧绿的叶片,让我心中的阳光再一次跃动起来。好像我的抽屉里还有我的那张画。我突然想到,于是急匆匆蹲下身子。一本书,两本书,我看到了略微泛黄的素描纸露出了小角。确实!我又蹦了起来,但马上又低下身,搬开教辅。
纸张却被压折了,中间被断掉的铅笔芯坐伤了,留下灰色的血液。绿芽被厚实的现实压着,倒了下来。绿分明不是绿,洒下的黄分明不是黄。他们交杂在一起,冲毁了最后一丝稚嫩。
我曾幻想着能描绘出最好的心中所热爱的世界,于是我不断地留恋与想象,去描绘它,但它展现出来的,无非是我人为对待他的心境。心中明媚,则由鹅黄与嫩绿;雨点催打,则是枯黄与铅灰。
这一次的阳光愣愣地停留在枯叶上,没有动。他明明是柔和的,但不是热情的。也许他在怀疑:那个经常往外看的小精灵去哪里了呢?
没事,至少我在这小世界中培育了一颗很大的果实。我趴在窗台上,看着窗外的树叶随着微风摇曳。我在这里!我向耀眼的阳光努力地挥着手。

88

91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