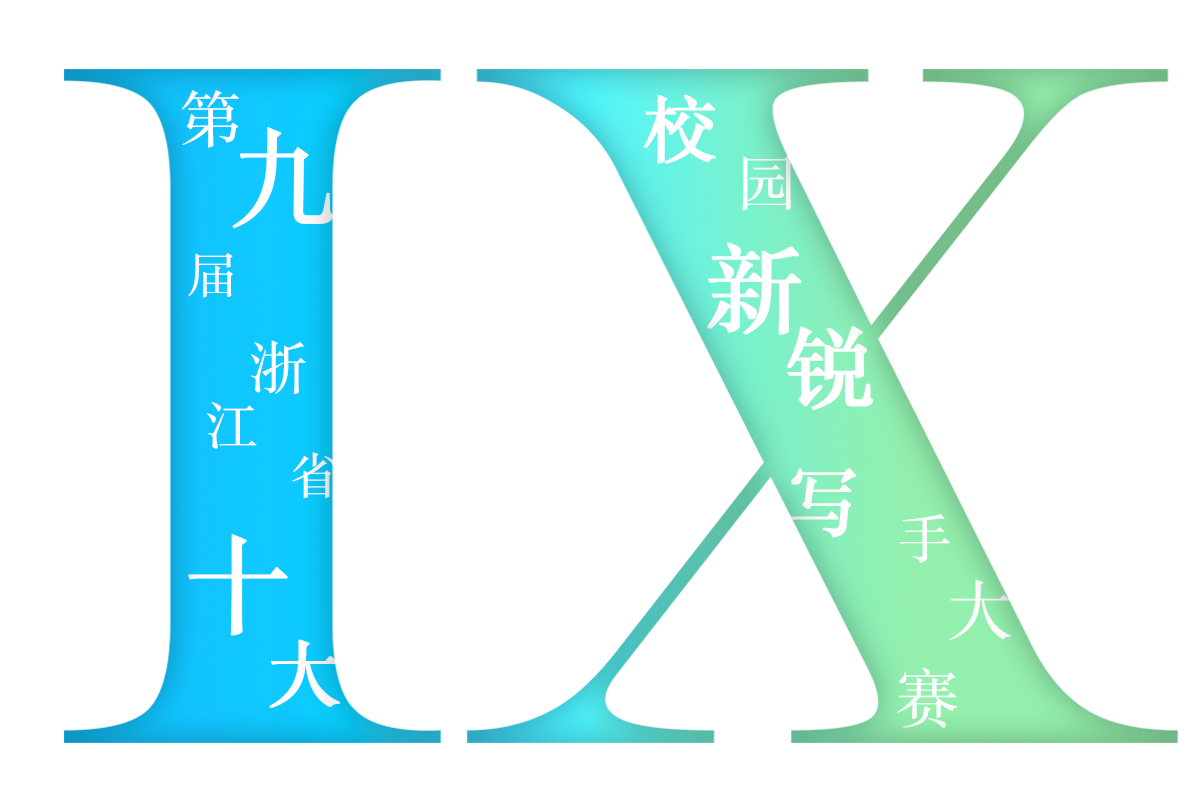小世界
lhyy 发表于 2022-10-01 19:09:23 阅读次数: 3翻过昨天的那页日历,下一张上的日期依旧被更大的红色油性笔迹遮盖着,“倒计时123天”——高三准确的日期早已失去了意义,只剩下一道计算和高考时间的差值的数学题每天在每个人心中演算着。
同桌看着我翻日历,轻轻搂上我的肩,无奈又颇有点打趣的说道:“哎,离我的小蝴蝶飞走的时间又近一天啦。”我只是对她的话习以为常地笑笑。
我就是她口中说的那只蝴蝶。大家都这么认为,我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也接受了这个称呼。
或者说是设定。
我开始确实是喜欢蝴蝶的。我那个背了三年的墨绿色的双肩包上别着一只有点“不合时宜”的黑白蝴蝶别针。虽然我也是全校基本上整齐划一的红蓝色校服中的一员,但我会在外套内侧的口袋里放一枚彩蝶胸针。还有我那个装满文具的笔盒的底部也贴上了小小的蝴蝶贴纸,很幼稚的那种。刚开始朋友会问我是不是很喜欢蝴蝶,我总是认生地用微笑回应,她们也默认我赞同这个观点。于是接下来我的生日礼物也是各种蝴蝶元素的小玩意。不知不觉,蝴蝶成了我这个十分怕生的人结交朋友的一个途径。
但仔细想想,我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或者说问过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蝴蝶,只知道让蝴蝶变得和其他元素稍微不同的开端是入学那天,父母和其他家长挤成一团,门口的保安像化学中的过滤漏斗一样尽力让学生和家长分离开,我和父母告别之后刚准备走,就感觉到手里被塞进一个软软的东西,是一只毛线蝴蝶,我回头看了眼不断朝我挥手的爸爸,还有皱纹里堆满笑的妈妈,忍不住笑了——这是我小时候在妈妈指导下织的两个毛线玩具中的一个。
又不是第一次离开他们了,怎么还把我当小孩。我想着。
有一次几个女生在课间聊天。为身边的朋友想个合适的外号。我安静地坐在旁边,一边抄写着数学公式,一边时不时听几句她们的聊天内容,她们也习惯了我总是那个听的人。我听到她们一致认为,我的外号应该是“蝴蝶”:
“你看你成绩一直那么好,上课永远不走神,下课还天天围着老师问题目,每个老师都喜欢你,也从来不给他们惹麻烦,而且你还那么喜欢蝴蝶,我看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合适的了”
“可是她不是引人注目的那种人,安安静静,两耳不闻窗外事,感觉没有什么事可以影响她。有没有那种透明的,或者颜色很浅的蝴蝶……”
我在话题转向其他之后,自行屏蔽了声源,兀自点了点头,我好像确实是她们说的那样。我习惯性地默念了一遍刚抄下的公式“空间内的直线关系只有三种,相交,平行和异面。”
我的高中生活什么戏剧化情节,迄今也没有什么波折,好像在这封闭的校园里,我唯一可以决定和落地的事只有学习。没有什么其他特长,我似乎没法说清十七年来学习的状态——屏着一口气,如一只振翅的蝴蝶,只想飞得越高越好,有时在峭砺的枝头稍作停歇,不知道终点在哪。而在压抑的高三,就算高处的气压会压断我的翅膀,我也要继续向上飞。
就像猫有九条命那样,我在不断减少的倒计时中,只想把蝴蝶所有幸运存活的机会消耗完,来保留最后在逆风中唯一向上的生命。
每个五点的远方初醒的凌晨对我来说比在逼仄的教室里的白天更火热,我站在宿舍楼的阳台上,在别人还在沉睡时,和爬满墙角的青苔与冷淡对视的教学楼一起背记生涩的英文单词。在匆匆解决完千篇一律的食堂早餐后,逃出闷热的教室,在走廊的尽头,面对着围着学校的那条河反复朗读着一页页已经泛黄褶皱的生物书,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我发现“和我作伴”的钓鱼的老爷爷也注意到了我,他钓上鱼的概率大概只有5%,可惜他不是姜太公,我也不是姬昌。每个下课没有嬉戏打闹,只有卫生间的人满为患或者教室的无人走动,甚至一日三餐的目的都变成了学习。深夜教室的最后一盏灯也是由我熄灭,回宿舍路上的贴着大字标语的路灯暗示的不是“归家”,而是几个小时后的重新开启的循环。
高三本来就是窒息的,我记不清是谁说的但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我盯着每张试卷上的红色数字,没有人认为它会下降,我仿佛也默认般不允许它下降。我不知道这种心理叫什么,直到我不经意间发现的一个词“蝴蝶的骄傲”。
但是我没看到后面的那句话“这是在被临死前也要挣扎着翅膀”。
我包上的蝴蝶别针在一次跑去食堂的路上掉了,外套里的胸针经过洗衣机的冲击也变成了一小块烂铁,笔盒上的贴纸翘起的边角已失去粘性,沾满灰尘。我没有在意这些,我的学习生活当然也不该受到这些的影响。我身上“蝴蝶”的标签还在。
但在那件事之后,只有我知道我的身上不再有足够的粘性去粘住这个标签。
在封闭的校园里,你没法知道外面的娱乐八卦,对我来说,甚至家也被默认成正在按既定的轨道运行着。但哪有什么既定的路线。
“我和你爸离婚了。”
妈妈强装镇定地说出这几个字。他们是和平离婚,妈妈所有的情绪波动都来源与对我得知这件事后的心情和对学习的影响。我也面无表情地点头,表示了解了情况。我什么话都说不出,话到嘴边都变成了肌肉记忆的古诗文和公式。
原本23个小时的假期变得格外漫长——我只想马上回到学校那个小世界里,至少在那里有我可以掌控的东西。我躺在床上,看着放在床头柜上的毛线飞蛾——另外一个毛线玩具
——两条直线从相交变成异面,真的是一念之间的事吗。
我把毛线飞蛾随手塞进书包。
回到学校,一切在时间的催促下不容得有变动,包括五点的凌晨,和钓鱼老爷爷相望的走廊以及深夜的路灯和打了鸡血的标语。但是试卷上的数字却不断减小,投影上Excel里的我的名字和第一列的距离越来越远。老师和同学觉得是我太紧张了,只是不断安慰我。我挤出标准的微笑,手里悄悄把试卷揉成一团塞进抽屉的角落里。我已经不会为成绩落泪,却会有一种似乎是成人才会有的被卡住喉咙的无力感。
原本觉得父母的分开对于即将成年的我来说只是如看过的电视剧情节一样成为上一季的剧情,但其实它好像在摧毁着其他的东西。摧毁着我在学校这个小世界里的自我定位。摧毁着我蝴蝶的外壳。
我真的应该是蝴蝶吗?
这个问题我用了几天看似照旧又打破既定轨道的时间去思考。
早起了半个小时,第一次看到四点半的凌晨,没有什么不同,只是雾更浓了些,甚至看不清教学楼上“明知致远”四个大字。青苔蔓延,记住用来装饰的花早已枯萎,腐烂的花瓣在晾晒的衣服滴下的水中以及融在泥土里,没有轮廓。而有一只蝴蝶似乎停在这花茬上酣眠。好像是我好几个月前看到的那只。蝴蝶总是被一切和花有关的事物吸引和停留,它能飞到的最远的地方在哪里呢?我猜它甚至飞不出这个学校。
从走廊的铁栏窗望出去,“姜太公”还在。空的水桶是他的结束,新的鱼饵是他的开始。我们之间只隔了一条河,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河边丛草高长,没有花香花粉,蝴蝶不会往那里飞,也永远过不了那条河。不知道哪里听过的,蝴蝶终究飞不过怒海,因为它只会接受极致的美丽的吸引,为极端的美而生,而死。不准许无厘头的失败,不准许离开既定轨道。
教室的最后一盏灯被我关掉,我走上那条熟悉的路。这次,我选择了靠近学校外面的那堵墙的一侧走。闪烁的车灯快速地消失在黑夜的尽头,校门口的那家夜宵摊的顾客也零零散散,剩下店主收拾碗具的碰撞声。值班的两个保安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这满街的实际都不属于我现在的这个小世界。我一步一回头地看着校外,没有高三的学生不会向往即将步入的学校之外的世界,或者说是对小世界的再见。
但谁又知道大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我好像从父母的一次次变道重置中窥探到一些——夜晚被闹铃打断,门外是困倦的阳光:蝉虫不响, 飞鸟不撞; 片刻的清醒稀释在床, 疲惫在公车中摇晃。灰色的城市像是个不眠的工厂,落花飘不进玻璃幕墙。 大人们只能安分地陪着平凡观望,而浪漫也只会陪着剧目中的诗人流浪。 他们可能不再憧憬向往年少的轻狂,向往的只是还会天亮。而我甚至在我这个经纬分明的小世界里手足无措,又为什么急匆匆地向前横冲直撞呢。蝴蝶在学校里活不过既定的生命,外面的世界又哪有它的容身之所。
我收回目光,看到路灯灯罩下几只白色的飞蛾围着灯光,不停往灯泡上撞。
飞蛾想要脱离黑暗,飞向白昼和光明,这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的真理。
第二天,我看到花坛旁的泥土里有一只翅膀已经半折,陷在土中的蝴蝶,它还在做最后骄傲的挣扎,纵使是徒劳。我轻轻将它踩死——是给它的解脱,也是给我最后的自视。
我不再学到头痛欲裂,不再被死板和极致的数字束缚,流逝的时间不再扼住我的喉咙,而是为我注入重新开始和前进的动力。
我手里拿着那个已经脱线的毛线蝴蝶和毛线飞蛾,来到面对河的那条走廊上。
父母把这只蝴蝶给我,所有人都认为我是蝴蝶。我又为什么要成为这只错误的蝴蝶。
我透过铁栏窗的空缝把毛线蝴蝶扔向河里。留下飞蛾。
后来,同桌在翻日历的时候照常打趣我,我把手搭回她肩上:
“我不是蝴蝶,现在只是只飞蛾罢了。”

88

93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