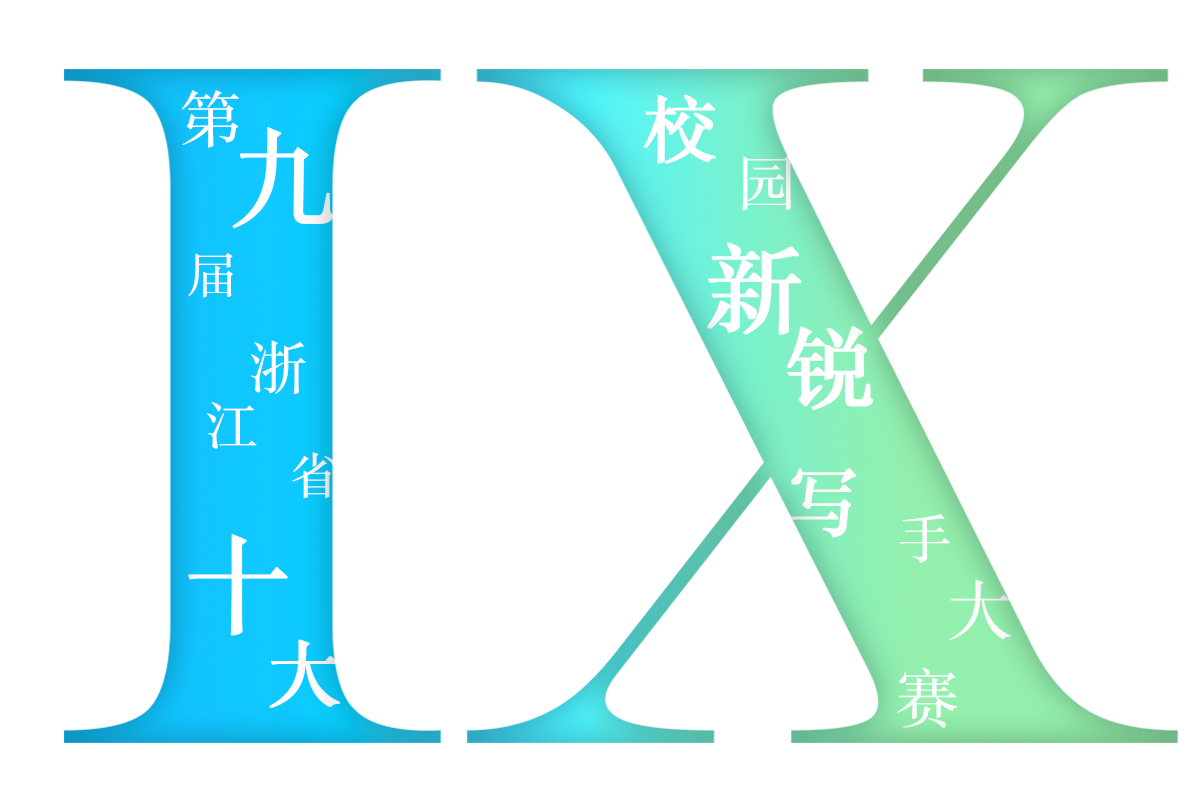飞鱼
叶楚馨 发表于 2022-05-19 11:27:02 阅读次数: 18073170
活鱼的麟。
那时候我们家门口的树发了疯,枝条都变得红彤彤的,火光跳动着,仿佛一颗颗罪痕累累的心脏。
“后来呢,那后来呢。”我扯着她的袖子问。
“没有后来了。”姥姥慈祥地看着我,她的脸枯槁得如同那棵树最后幸存的皮。
但我相信是有的,从那以后妈妈就住在我们墙上的相框里,相框的裂痕和墙的裂痕连在一起,多么融洽。她还是戴着那副细框眼镜,眼里闪着温柔的光。镜框是黑色的,妈妈的脸是灰色的,衬衫是白色的。
有时候她会从相框里走下来,用她深灰色的唇亲吻我的脸。风扬起我小木床上的蚊帐,那上面有很久以前干涸了的蚊子血。蚊帐被钩子勾着,那钩子很锋利。
这时候妈妈总怜悯地看着我。她说:“这木床的四角缠着蛛丝。这蚊帐上有斑斑点点的暗红色。这钩子,它……太钝了。”
“钝?”
“是啊,钝。”
妈妈及踝的长裙在风中飞舞,她裸露的双足有一点透明,上面还有星星点点的斑。姥姥放在铜盘里的三只白蜡烛上荡着很烫的焰,它们一摆一摆,像三只忧心忡忡的眼睛。
我看向窗口,窗户晃荡着。是风,风太大了。我向窗户走去。
妈妈说,不要关窗,让风把空荡荡的夜晚塞进屋子里来。还有那玫瑰色的天空,没有什么能缝补它的裂口。
于是我回去收起散落了的蚊帐,那钩子戳了一下我的手。一点也不疼。
妈妈面带笑容地咬啮着她的指甲。她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去问姥姥吧。”我说,“我不知道。”
“你爸爸说要给我换一个相框的。”她揉搓着那些不长不短的指甲,叹息,“这相框快要破碎了,这墙也快坍塌了,我每次都撕扯着它们,想把自己的身体从桎梏里解放出来。”
我问:“你还记得那棵老树吗?”
她说她记得,她和它一起咽下了这片天空的最后一只太阳。
那是一个冰冷的夜晚,她用尖尖的虎牙碰了一下那团火球,然后它颤了一下,哗地散开。
床边的那只花瓶告诉我,这儿的地心烧着一团鬼火。
“鬼火,鬼火是什么?”
“是蓝色的,是地心的阳光。”
“那天空呢,天空是什么颜色的?”
“玫瑰色,那上面有太多的裂痕,所以才漏进来光。”
“为什么要有光?”
“你爱你的妈妈吗?”
“爱。”
“那你还问什么呢?”
光不太好听,它像是每天深夜姥姥踩着咿呀咿呀的木台阶上楼,然后喉咙里呛出凝滞而浑浊的咳嗽声。
我用指甲敲击着那只已然不置一物的花瓶,它的响声多么清亮。
哗——
天亮了。
姥姥拉开我屋里的窗帘,阳光刺得我眼睛发疼。
她说:“阿幺,这花瓶太空了。阿幺,别再睡了,那桌上有我替你挑选的书,你要读完它们。阿幺,我是为了你好。”
我走到桌前,那书压得如山一样高。
我知道我不曾睡去过。在这漏光的屋子里,每一片瓦都在屏息谛听各处的妄言。真实,没有真实。
姥姥干枯的手指覆上那相框,她又在咳嗽。“这相框太旧了,不能在挂在外面,得放起来。”她一边说着,一边颤巍巍地取下它,把它锁在桌子的抽屉里,那锁上纹着一只麒麟,它的双眼狰狞,像是两团烛火。姥姥掂了掂锁,将钥匙挂在脖子上。
“你爸爸说去找一个合适的新相框,等他回来了,再把相片挂出来。”她又咳嗽几声。不多时,她往花瓶里放了一枝新折的桃枝。“桃枝辟邪。”她这样说着,伸手抚了抚那把麒麟锁,一步一步缓下楼去。
那高高的书堆挡住了窗口,书的间隙因此显得格外明亮。姥姥要我在这里用薄薄的纸页捆缚自己。
“那之后你便重生了。”她这样说。
书堆是顷刻间倾塌的。它们纷纷扑打在单薄的木地板上,发出乏力的声响。
一只飞鱼从窗口飞了进来,撞倒了花瓶。它是蓝色的。它的翅膀尖尖的,但我知道那很钝。
抽屉里有细碎的声音,相框裂开了罢,那脉络从一端连向另一端,沉默地潜行。
“你姥姥不慎将麒麟锁的钥匙遗落在水井底。”飞鱼说,“另一把钥匙在你爸爸那里。你不想去找吗?”
那花瓶仍是完好的,我把桃枝丢出窗外,将飞鱼装在瓶里。我另折了柳枝,将它从缝隙间塞进抽屉。柳枝招魂,这大概是对的。
离开时我仰头看了看天空,那玫瑰色的边缘仿佛结着褐色的暗痂。
我知道打开那抽屉不只有一种方式,但我想也许这会是最好的方式。
爸爸在南边,于是我向南走。
在密林中我找不到更窄的路。我害怕路上的每一只萤火虫,它们都想钻进我的耳朵。
飞鱼扑打着翅膀,林间是未拼凑完整的月光。
“是月亮。”我说,“没有了太阳,这么会有月光呢?”
“你以为这世上只有一只太阳?”
“难道不是吗?”
“不,有无数太阳,一只消逝了,又一只便升起,没完没了。天空不缺阳光。”
“那玫瑰色的天空呢,那褐色的纹路是什么?”
“那是阳光,你看不懂的阳光。你爱你的妈妈吗?”
“爱。”
“那你还问什么呢?”
爸爸住的地方叫空空镇,一点也不空。这里的每一条路在曲折之处都裂出一个宽大的断口。我俯瞰它的凹陷处,看见一团蓝色的絮状物。它伸出无数的触手,有一点亮。
大地上到处都是悬浮着的房屋,它们在大风的鼓舞下碰撞,碰撞,在跌宕的声响中,抖落一身沙尘。
飞鱼说,我爸爸就住在那扇绿色的小门里。
过了很久,那扇门在我眼前打开,我的肩上簌簌地落满了碎沙。
爸爸手里拿着一块布,正小心地擦拭着一只相框。
这屋子里的墙上,挂了数不清的相框,相框和墙壁在无尽的碰撞中一同损坏。
这些相框的玻璃被擦得好亮。嗤啦,嗤啦。细细的裂纹找着一个出口,就开始疯狂地蔓延。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去,妈妈的相框呢?”
他的指间支着一根烟,白烟升腾而起,聚成一朵托着屋顶的云。他说:“这里的相框太多了,我找不出最合适的那一个。”
“它们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任取一个呢?”
“不,你不懂的。你爱你的妈妈吗?”
“爱。”
“那你还说什么呢,回去吧。”
房子的窗口淋满了雨水,我向手心呵着热气,我的手心凝结出一朵云。窗外面的天上有微弱的褐色阳光,逐渐失色的天空正给予它养分。
“他不爱她。”飞鱼说,“他不爱她。”
爸爸从箱子里取出新的相框,将它们换上。他裂开嘴角,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你知道这里没有日出日落吗,天空中的太阳在那云朵后面一天天地替换,但它永不落下,自然也永不升起。你看那褐色的阳光,它是没有爱的。这座小镇上的人们,都是没有爱的。当人们失去了爱,就变得冷静,他们的生活有条不紊。”
“那我呢?”
“你?我十多年没有见过你了。”
这地方是那么暗。外面的天空也那么暗,它吝啬地赐予人们那冰凉的阳光,悸动他们的躯壳。
可我的心里像是有一只太阳,它散发着新鲜的光,有时是耀目的白芒,有时是一团火焰。我听见自己砰砰的心跳声。
小镇的雨忽然停了,窗口的雨水无影无踪。地面一下子从潮湿变得干燥,接着它裂开了口子,冒着烟。一幢楼从不远处飞来,与爸爸的屋子碰撞在一起,墙壁上的相框扑嗒扑哒地唱起歌来。
我看见外面的天空微微亮了一些,云层背后裂开更大的口子,褐色的纹路开始变得半透明。那口子也许漏风,因此云朵焦虑地晃荡起来。
“水。”爸爸嗫嚅着说,“这小镇将逐渐失去它拥有的水。它要变得干巴巴的,像一张枯皱的纸。”
爸爸说,他要上楼去看看屋里剩下的水。在我挪动我的步子时,他拦住了我,不让我上去。
我问他,老屋麒麟锁的钥匙在哪里。
“忘了,我忘了。”他挣开我的手,逃上楼去。
然而我是不得不去寻找那钥匙的。我踮起脚尖,顺着那扶梯盘旋而上。右手边的墙上挂着一框框的画,每一框画里都有一只黑猫,它们宝石般的眼睛熠熠生辉。那光多么冷,仿佛里面住着一座千年冰山。
楼上有一条窄窄的走道,尽头是一扇木门,那上面的锁已被打开。
我正向着那门走去,飞鱼却说:“停住吧,看看你右手边的房间。”
这个房间甚至连门也没有,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一只没有出水口的缸立在房间中央,里面的水一点一点地变少。许多幼小的黑鱼躲在缸底,它们的尾巴甩动着,缸快要见底。
“水呢,”我问,“水到哪里去了?”
“没有了,消失了。”
“那这些鱼呢,它们就要死了吗?”
飞鱼说:“不,鱼不一定要生活在水里。没有水,鱼可以生活得更好……看,钥匙在缸底。”
我捡起钥匙。它是干的,缸里已经没有水了。那些黑鱼甩动着尾巴,它们的背上长出坚硬的翅膀,一只一只飞出了房间。
我听见楼梯口的画框落在地上破裂,屋子里响起诡异的猫叫声,那沉闷而压抑的呜咽,仿佛从冰山之下传来。
我窜下了楼,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摘下一个相框,就不再回头。
返乡的路上,一队马车自远处而来。枣红色的马,灰色的车,放眼看去,所有马车尽是如此。不断被风掀起的帘子后面露出一张张刻板的脸。马车里的人们都将双手交叠在两腿之间,他们的嘴角噙着虚设的微笑。他们的腰上束着牢固的铁链,让他们与马车不再分离。
“那些人被困住了。”我说,“为什么呢?”
“不,不是人。”飞鱼答道,“他们是假人。假人的腰上都有很深的勒痕,因为那里都曾被锁链深深勒住。”
“可是,为什么要有假人?”
“生者不愿辞世,便每日用锁链将身与魂紧锁一次,那锁链在黄昏时一点一点收紧,子夜来临时,那勒痕最深。在那时解开锁链,假人又一次重生。”
“为什么?”
“因为牵挂。”
我又想起那吱呀作响的木楼。姥姥提着她的竹篮回家时,篮里不知是什么在叮当叮当地嘤咛着。她那双旧了的布鞋有着薄薄的底,鞋底曾经踏过了那夜晚平整的月光。
现在正是黄昏,可是天却越来越亮。那红褐色的裂纹有些发白。是太阳,太阳要在天外醒来了。
那古旧的木楼沐浴着这侥幸的光,老树的根在地底跳动。
我打开了抽屉上的麒麟锁,里面的相框已经完全破裂,一片厚重的玻璃压在妈妈的脸上。她急促地呼吸着屋里的空气,神情疲惫。我给她换上了新的相框。
妈妈说,“把我藏在一个更好的地方吧。”
于是我抱着她的相片在木楼里四处走,踏起角角落落里轻飘飘的尘埃。然后,我听见姥姥的咳嗽声。她踩着那双薄薄的布鞋,腰间的锁链拖在地上,叮叮当当地响。
子夜还没有到,姥姥没有挎着那只竹篮,窗外也没有朦胧的月光。
我抱着妈妈的相片躲在床下,听着那锁链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姥姥翻动着木楼里的物什,她呼喊着我的名字,木楼嗡嗡作响。
妈妈问:“你爸爸呢?”
“他在空空镇,一个没有爱的地方。他不会回来了。”
“那我就不再等了。阿幺,你是个大孩子啦。你为我上色,再吻一吻我吧。记得把我放在后山的坟头,沉睡已久的太阳就要出来了。”
我听见墙头的裂痕嗤啦一声加深,细小的木屑落在姥姥的鞋边。
她说:“出来吧,阿幺,我只想和你说说话。”
我探出头,看见铜盘里有三只白蜡烛,烛泪正不停地落在盘中,大概是烫的。
“我感觉这木楼里的事情渐渐安定下来了。”姥姥的声音苍老而又慈悲,“天上的太阳沉睡了那么久,总有一天要醒来。那么我就与你道别吧,孩子。天空会渐渐地发白,而你,你将得到我的祝福。”
姥姥解下她腰间的锁链,她的腰上有一道深深的勒痕。
黑色的发,红色的唇,白色的衬衫。我放下手中的画笔,开始凝视妈妈的相片。让我上色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啊。
如她所愿,我轻轻地吻了她的侧脸。
那时候天空正渐渐发白,沿着褐色的裂痕,那沉默的玫瑰色一点一点地消失殆尽。飞鱼扑打着翅膀飞出了我家的窗户,落在木楼门口老树的枯枝上。
我将妈妈的相片放在了后山的石碑前,那不远处,是姥姥的新墓。暮春的风摇曳着满山的丛林,看起来迷蒙而悠远。
山下有一条河流。
在十岁以前我常常做一个梦,梦里面有这样的青山,山下的河流里有好多青黑色的鱼。妈妈坐在岸边垂钓,长长的竹制鱼竿上挂着新鲜的饵。那鱼钩很钝。
有一只鱼向着那鱼饵游去。它的身上有闪闪发亮的鳞片,背后的两只翅膀收着,看起来很安逸。哦,原来是一只飞鱼。
我将手伸向那只鱼钩,避开钩尖,紧紧地握住它。我晃动着它,一圈一圈的涟漪在水面漾开。飞鱼在我的耳边说,天上有一个太阳的时候,水里也有一个。两道光芒中总有一道俘获了你的眼,接着你朝着一个方向去。你在柔软的水草之间摆动着身体,水中的光芒多么明亮。然而你要去一个地方,你要去一个地方。
那竹竿轻轻一提,我便浮出水面。
我看见暮春的阳光下一张模糊的女人的脸。我听见一个苍老而慈悲的声音说:“看,是个女孩。”
“你爱她吗?”
“爱。”
“那么,还需要说什么呢。”
那个声音似乎由天外而来,无始无终。
我在山上回望,我感觉大地之下有一阵难以平复的脉息,它在地心点亮了一团蓝色火焰,火焰向着四处蔓延。
裂痕像藤蔓一样在那陈旧的木屋上扎根生长,接着我看见那屋顶颤抖了一样,历经了百年风霜的古屋在顷刻间坍塌。我看见老屋边上的那棵树,它在十多年前的一场劫难后便不生不死,吞吐着这山下的荡气。
一只飞鱼忽然从树枝上振翅而起,飞向天穹。它像是一团火焰,待远了时,又化作一片白芒。
我终于明白,那无怨无悔地俯视着大地的,不是太阳,而是一只飞鱼。它可以没有水也可以没有天空,但它永远无法失去翼上那亘古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