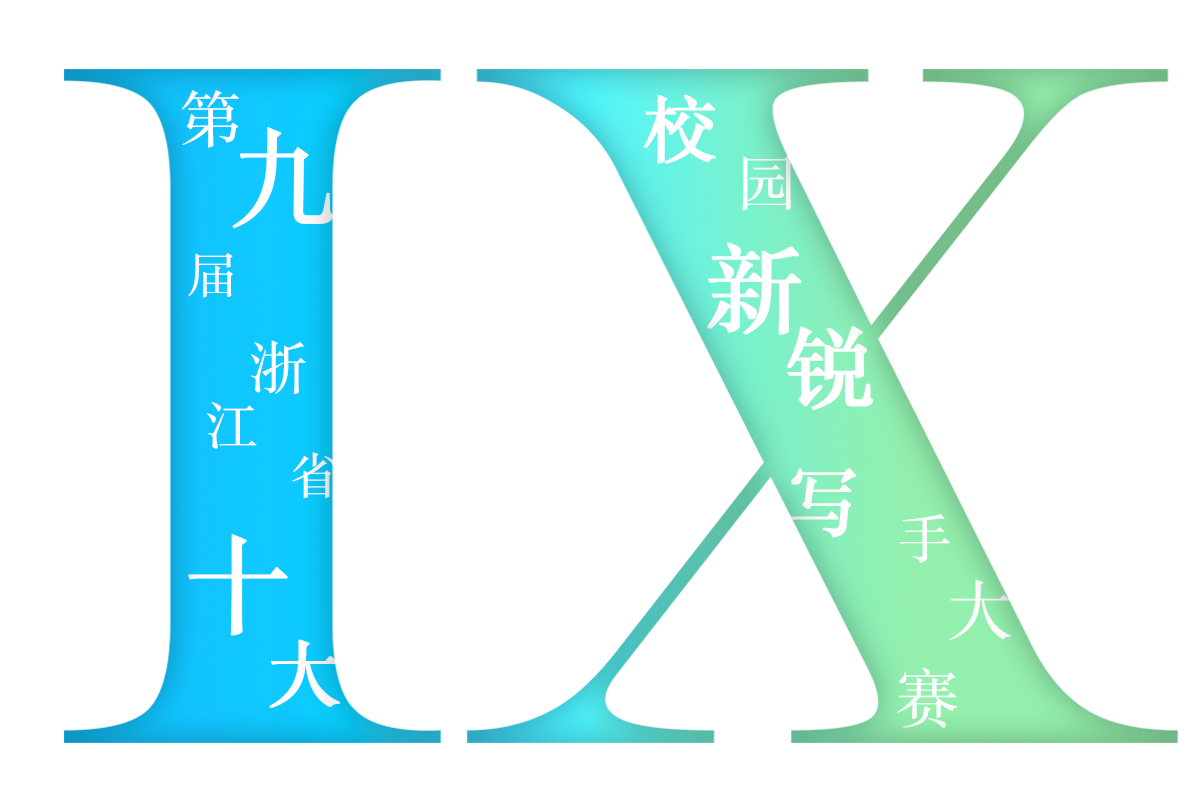品香的喀布尔人
吴泽浩 发表于 2022-05-19 11:27:55 阅读次数: 8824709我很早就认识他,他的铺子就在我家对面。
这间铺子与所有其他神奇的铺子一样拥挤、杂乱,你一走进就会意识到,它独特的主人正在等待值得招呼的客人。温黄的灯光冲洗深色的实木地板。皮鞋一动便响起嘎吱嘎吱的木头声音,似乎是来自某件正值出售的香炉灵魂的问好。连着墙壁的木头书橱挤满香箸香碳;木格子里垂挂下线香,像荷着沉甸甸露水的柳枝。但那么多的线香探出身子,不得不说更像是疯长的水草。如果再在角落的木桌子内侧,放置一个倔强、精瘦、头发花白而微蜷、怀旧的老人——铺子合适的主人——那么一切营业的准备就都到位了。
陈伏寅香道用品店,正对着一家香水店。
陈先生正狐疑地打量着那个满地乱爬的小家伙——尽管是在脑海中,他的目光依旧清晰厉害——这种目光的对象通常是难以摆脱的麻烦,或者是某种不熟悉甚至不耐烦然而不得不接触的事物。“一个丫头,”他是这样念叨的,“一个邻居家有事而不得不寄托在这里的丫头。”他特别加重了“邻居”两个字,似乎是要说明无法推脱的原因。“一个多年的邻居。”他又补充道。这样自言自语一番以后,他那颗厌烦吵闹的灵魂终于无奈地屈服了。陈老头重新看着小家伙,带着童年般的浓郁好奇。
我瞪着两只大眼睛,并不明白对面的老头刚刚说服了深处的自己,也不清楚这个开始对于我有什么意义。我看着什么,又什么都没看,因为实在记不起那时的眼睛倒映了什么颜色。不过鼻尖记性倒不赖,时至今日还能从脑海深处调出那时上好的檀木香。接下来是嘎吱嘎吱的声音,陈老头走进黑魆魆的楼梯口,在潮湿狭小的阁楼上逛了一圈,小心翼翼地将一块沉香粗坯摆在我面前,又把一瓶脏兮兮的开了口的香水扔到对面。也许他是想从我这得到安慰,也许仅仅是出于好奇。接下来他眼角上拉链似的皱纹拉开了,嘴上也有了笑。这不是摆脱了棘手的麻烦的笑,而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他抱起小手中抓着木条的我。
我把胖乎乎的小脸往他的胡渣上蹭,一瞬间喜欢上了这样做。
“水奈,你为什么选沉香?”他总是这样问。其实我根本不记得这件事,全靠老头的讲述来想象。
“因为沉香味道淡淡的,时不时冒出来一下,像一只黑色的猫咪绕着屋子打转。”我这样回答。
第二次被存放在香道馆是多年之后。那时人们对香起了些兴趣,于是香水店胖了一圈,陈先生的铺子便相应地窄了一边。他只能卸下一侧的壁橱。这样就更乱了,有些乡下小中医铺子的感觉。陈先生的坚强和倔强下面生长了一层疲倦,白色的发根从这层土壤噼里啪啦往外冒。
我已不记得这个儿时相处一个月的玩伴,流露出八岁女孩的羞怯。但陈老头记得我——一个有缘分的丫头。他经常买些糖果给我。靠这种有力的贿赂,我们重续了过去的友谊。
我们在一起玩、品香、看书。每当夜晚降临,外面繁华一片,各种喧闹;小铺里就静静地焚起一炷香。淡淡的甜甜的香味像是枝蔓在伸展蔓延,温柔地缠绕住灯盏和木具。一会功夫,铺子就变成了不逊于森林的绿色世界。陈老头笑眯眯地倒在安乐椅中,眼睛眯细成缝,惬意地瞧着我踮脚在藤蔓中间蹦蹦跳跳。椅子一摇一晃,和老爷钟的滴答声携手共舞。这时候无论谁喊他,他都和不会动了一样,只有胸部一起一伏,鼻梢还在缓缓地吐纳,安详的表情如同醉倒在午后的阳光下。我总是觉得,这时候的铺子就像一条离岸的小船,置身于岸边的灯红酒绿一片辉煌之外。慢慢地、慢慢地,喧闹的海岸消失了,与航灯相伴的只有一片静谧,足以自慰的是大海的温柔与古朴。
我常常要求听故事。像这样的老头是不会有什么故事的。他讲完了中山狼和东郭先生就没辙了,于是从《香谱》和《中国香文化》中抽出一本泰戈尔的小书。我们一起读《河边的台阶》;我们都最喜欢《喀布尔人》,为了伤感的结局唏嘘不已。我们之间的绰号很多,有时随便想到一个就随口说出。一次我看着他高高瘦瘦的身影,几乎就要喊出来了,却被他抢了先。
“敏妮,小敏妮!”他轻轻呼唤。
我咯咯笑着大声回答:“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我们真是一对好朋友。
陈老头如果能用这种态度对待消费者就好了。他经常粗暴地从像摆弄廉价香水一样摆弄精制茶炉的顾客手中夺回香炉,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净再放回去;大声呵斥那些随意拨弄线香和翻动香道书籍的人。他像照顾父亲一样呵护香具。他简直不希望不懂行的人进店。他冷清的生意很快更加冷清。
这次寄存也只有一个月,但我们的友谊没有断。我尽量节省零花钱,有空没空就往铺子里跑,趴在柜子上盯着圆柱形香炉和仿古的博山炉。陈老头总是便宜地卖给我。这个年纪的小姑娘是不会变化也瞧不出变化的,但记得有一次我甩动着大条线香,兴高采烈地说:“喀布尔人,这是人工香、人工香,你说过不卖的。”
我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和他共处的一个月里,每当下午一两点钟,对面香水店人山人海、刺鼻的香味勾住行人、女士们急着把自己打扮成虽然容貌上差一点但是香气上不输于玫瑰的花的时候,我和他就坐在半闭的卷闸门里(这样没有空调的小店也能享受一下午的阴凉)。陈老头取出一只错金香炉,拨开雪一样的香灰,将烧得通红的香碳塞进去。香铲铲出一个香灰圆坛——圆坛的厚度很有讲究,沉香薄些,檀香厚些——用香箸戳个直通炭火的小孔,打出美丽的梅花香筋。接着插云母片,盛上杂糅的香丸。白线笔直升起,如同一条极细的吊绳从香丸中被拉出来。很快香气就从意想不到的地方钻出来,有时像只轻快的幽灵在屋中飘荡,有时像锥形灯罩笼住整个空间。陈老头就在这时候传授香道知识,教我怎么区别沉香和檀香,或者沉香和龙涎香。他对人工香和电子熏香炉特别轻蔑。“这些都是为了偷懒和便宜而发明的,”他说,“真正追求香道的人都不屑于使用。”每当有顾客要求这两者,他就表现得更加冷淡。
可如今他在卖人工香,我像抓住小辫子那样兴奋。
他十分尴尬,脸涨得通红,灰白色的胡渣不安地抖动。他的一双大手绞在一起,没有话说。那些时候的变化一定比我注意到的多得多。
搬家之后,新小区里有很多同龄的玩伴,我不久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便不太去找陈老头了。我是个念旧的人,但那时是这样一个年纪:我会哭会笑会闹脾气,不过都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我的心里不装东西。
那段时间记忆最深的一次铺子正午便关了门。但这难不倒我,我知道从哪儿可以钻狗洞进去。铺子里亮着一盏高悬的油灯笼。支在地上的电扇咣当咣当直转,把地板踩得一深一浅。鼓出的风托起灯笼垂下的流苏,像一条油亮好看的马尾辫。一下子忆起体育课上精瘦的男同学一脸严肃,告诉我看女生跑步时辫子一甩一甩的格外有情调,忍不住笑了出来。
“水奈,是你吗?”苍老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急忙走到亮处。陈老头显得憔悴,没有以前精神了。他一定为铺子操尽了心力。我有些难过。我知道他不会让铺子垮掉,这个决心他向我表明过。小城里曾经有三家香道馆,现在另两家都成了大的和更大的香水店,只有他在苦苦支撑。我猜他是担心有朝一日不佩戴几个香囊便显得没有品位的时候,人们会无处拾起这门艺术。他是个坚强,但也确乎幼稚的老头。所以有时看见他弓着腰,揪心地看着客户翻来覆去地掂量香炉,在上面放肆地印着指纹,我也不觉得奇怪。他会在歇业之后心疼地擦拭香具。白天他把灵魂像晾衣服一样晒出去,晚上再小心翼翼地收回来叠好,修补被狂风刮破的地方。他只是想撑着这个铺子。
“水奈,过来帮忙。今天要做鹅梨帐中香。”老头正细细地将沉香木捣成粉。我闻出这是上好的沉香,近几年很少见了。呵,老头拿私藏出来了,我想。一定是重要的事吧。那时大人们开始用“懂事”来要求我,我当然乖乖地跑去香案上研梨。
“喀布尔人,你今天好用心哦,从没见你这么仔细地做香。”
“老实说这些古方做了这么多遍,闭着眼都不会出岔子。但这回是要送给一个朋友的,一定要顶用心。”老头顿了一下,又说,“是西安一个老太太,也是资深香友了,从前阔绰的时候收藏了一对清代的碧玉麒麟钮云耳香炉,经常借给朋友们。老头我也用它们熏过一个夏天的檀香,那滋味——啧,啧。现在还想得起来。好炉子就是不一样。这几年她生意不景气,落魄了,还是不舍得卖,说是要死后捐给国家。万一哪天她过不下去了,把炉子卖给随便一个贪财鬼,那就糟糕透顶了。圈子里的朋友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老头没什么钱,只能做些香寄过去。”他说的时候很有些兔死狐悲的感伤。
“你的香是顶好的,比他们的钱值钱多了。”我狠命地把第二只大鹅梨捣成汁,动作夸张,想逗他开心。
“别说了,干活吧。”他勉强笑笑。
我还记得他有一次感慨地对我说,香道是一门被遗忘的艺术,一门没落的艺术,购买香具的都是些小圈子里的朋友。而他对朋友总是很大方,经常送些香,或者把那只珍藏的错金博山炉借出去。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他这买到了便宜货。我曾劝他不必对朋友如此客气,他的回答我当然记得:
“唉,现在很少有人会花一下午时间品香了。老头总忍不住便宜点卖给他们。”
十只大梨都研成了黄澄澄的汁水,和一两磨得百目细(指原料颗粒的尺寸)的沉香粉末匀成香泥,摆进银器中——这种香用银器蒸才最正宗——装进甑里,坐在水锅上。我和他围坐在锅子边上,模样像是围坐在无垠沙漠的唯一一棵大树底下。风沙吹响树叶,发出沉闷的声音,是无烟碳滋滋地烧着。陈老头不时掀开盖子。梨汁终于蒸干了,他把香泥拉成一条笔直的线,铺在香案上烘干,用小刀等分。粘上香泥的小刀突然顿住了,陈老头拈起一截香,怔怔地出神。他身后是昏黄的灯光。
这是我对铺子的最后印象。
我和朋友从电影院出来,进了西餐厅;从西餐厅出来,又去唱卡拉OK。这些事在同一幢大楼的不同楼层有序地进行,为着庆祝高考结束。我还特意喷了香水。等到我们从歌厅出来,庆祝的流程彻底完成了。我们终于成为了老师口中的社会青年,再也没有力量阻碍我们穿高跟鞋、烫发和涂指甲油了。
走出大楼的阴影,我忽然发现今天是个天气很好的日子。线团样的白云拖着尾巴。也是那么忽然,我想去看看陈老头。虽然意识到了会有的尴尬,但还是想去看看。铺子就在这条街上。
已经很多年没有去了。繁重的课业使我抽不出整片的时间品尝这古老的香味。而品香这件事你做得匆忙了,会觉得还不如不做。
更重要的是,流行歌曲和通俗漫画更多地占据了我的心。这些为我们的审美量身打造的什物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步入暮年的古典艺术。我还是不可避免地疏远了香道。
我有些愧疚,但我也知道这是没办法的。我不知道老头如今怎么样了,我甚至不知道铺子还在不在那儿。
我摸着不知名的树一路向前,每一步都多几分犹豫。我终于还是站在了铺子前。铺子似乎没有大变化,只是当初意气风发的楠木招牌泛出了黄色。陈老头戴着老花镜,模样有些滑稽。他似乎没有预料到我会长这么大,他一定相信我还是从前那个样子。接着他认出我了,脸上有了笑。
“水奈……”他突然愣住了。显然,他闻到了我身上的香水味。两条法令纹显露出来,他还是轻轻地呼唤:“敏妮,小敏妮。”这总能引起我热烈的回应,但我不能像从前那样回答他了。
这样的见面让我俩都没有话说,尴尬在寂静中滋生。寒暄几句,我飞也似地逃出来。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地回答他。我这个小敏妮和那个敏妮一样长大了,不能再重温过去的友谊。而他却像刚出狱的拉曼——那个喀布尔人——以为世界多年未变。
他该回家了——就像拉曼回到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女儿在一起——他也该回家了,回到那个能默许他的灵魂和他的艺术的地方。